

法国哲学的“前理论”状态
——兼论《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回顾20世纪法国哲学的发生历程,最容易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莫过于雷蒙•阿隆借着一杯酒向萨特介绍现象学的时刻。萨特在访谈中对自己的激动之情寥寥数语,但波伏娃却用了不少的笔墨去完整地讲述那个心灵深处所受到震动。[1] 并且关于这次对话,两个人的回忆稍有不同。波伏娃如此回忆阿隆的话:“如果你是现象学家,你就能谈论这杯鸡尾酒,这就是哲学!”而在萨特的印象中,阿隆说的是“(如果)我们能够推理这杯啤酒,(那么)最终这就是哲学”。我们可以把到底是什么酒的问题留给精神分析专家,只是专注于这杯酒前的动词:谈论(parler)还是推理(raisonner)?从字面上看,“谈论”显得比“推理”随意很多,缺少后者在过程中的严密性和逻辑感,同时也就缺少了整个过程“最终”所达到的哲学性结论。萨特透过现象学看到了相比于其他研究,哲学思考在面对具体对象时自我展开的独特方式。而波伏娃则更强调这种思考过程既要面对日常事物,同时又要超越传统的哲学思维,更重要的是,这种新哲学还要付诸于话语实践,那么它就应当以自然的谈论姿态作为开始,这样才能穿过术语触及对象的真实存在。当然萨特和波伏娃都坦言,他们所继承的哲学理论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思想对于这个世界的关切和追问。现象学提出了“朝向事物本身”的哲学使命,在此刻鼓励着他们重新获得思想力量的尝试。不过,萨特并没有坚持由胡塞尔所展开的意识结构的研究向度,他要求哲学直接谈论具体对象,同时也要求哲学表达出日常世界内在意义的复杂性。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哲学就必须暂时放弃惯有的普遍性话语,放弃理性的超验性地位,而重新探身于经验的动荡之中,在非对象性的关系中重新探索思想的支点。简要地说,就是降低哲学对于纯粹理论的追求,提高哲学对于现实的解释能力。

萨特在酒杯前的顿悟颇具法国哲学的典型性,也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理论发展。《存在与虚无》中的“咖啡馆”、《知觉现象学》中具身化的“保罗”和“皮埃尔”、《词与物》开篇中博尔赫斯小说所引起的笑声、《意义的逻辑》中持续出场的卡罗尔童话中的逻辑悖论——20世纪的法国哲学主动舍弃哲学论证所要考虑的对象性同时也是客观性(objective)的分类原则,或者说他们并不在意学科间的分界,在哲学、社会学、心理学、艺术学和文学等等领域往返穿梭。作为当代法国哲学界的带头人,巴迪欧抱怨康德,因为后者设置了“理性的局限”,而在前者看来,理性是没有界限的[2]。理性表达了思想的力量,坚持理性的无界就是坚持思想的自由运动,而最高程度的理性是要求思想在穿过世界的厚度的过程中生成真理。当然巴迪欧对于真理的期待并不只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抽象真理,而是具有开放性的思考方式,且最终要达到生活的层面。无论是出于参与实践的使命感,还是保持思想的解释力,法国哲学中总是散发出感性的气息。甚至在其进入现代性的开端之时,就已经透过深浅不一的文学色彩而表现出感性的自觉,比如《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炉火旁或者睡梦中的怀疑”或者《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对于自然状态的感性假设。就哲学所呈现的不同的理论成就而言,如果说德国哲学所教授的思想体系让我们陷入到思辨的宏大版图之中,那么相应地,法国哲学在经历了启蒙运动之后,则是重新思考理性的普遍发展中潜在的独断论,故而他们的写作有意识地要摆脱理论的负担,保持思想在经验平面上的自由流动。法国哲学调动自己的想象力与观察力检视每个遇到的对象,对之展开阐述,而非规定。而这种思考方式,我们将其阐述为“前理论”状态。
我们用“前理论”说明法国哲学在逼近实际生存状态的过程中所迸涌出的丰富的研究向度和写作风格。在一般的理解中,作为理论形成的预备阶段,前理论的研究任务在于提供素材、汇集数据或者罗列元素等基础性工作,而这些材料最终经过筛选、排序、整合等一系列的抽象工作逐渐被组织成理论,形成确定的结论。故而,如果只是停留在前理论状态就会有“理论能力不足”的嫌疑,毕竟研究能力自我证明的最直接方式仍然体现在所包含的观点的自洽性、所达到的结论的深刻度、所构造的体系的全面性等方面。换言之,我们对于理论总是持以形而上学的要求,期待着通过理论实现对于经验的超越,安然伏身于结论之上就能把握、控制经验。长久以来,哲学的书写方式都处于这种理论自觉之中,直到其再也无法补全破碎而分散的现代性图景。究其根本原因,我们一方面认识到以技术为内核的现代性发生的复杂局面,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在理论内部,我们既已丢失曾经继承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未能打开思想的包容力。在此前提下,继续固守理论的界限将会加重哲学研究的萎缩。也许“前理论”作为策略,提供了探索哲学与现实的新的可能性。
前文借用法国哲学中的文学色彩显明其“前理论”状态,除了文艺之外,法国哲学对于其他学科也是旁征博引,大加发挥,比如《临床医学的诞生》中对于医疗资料、医学知识的借用,《反俄狄浦斯》对于精神分析理论的介入。法国哲学的书写中还广泛地表现出数学情结,从笛卡尔的坐标系到巴迪欧的几何学,数学示例使得他们的论证简洁直观。无论是通过介入某个领域从而提出哲学性的观点,还是策略性地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法国哲学对于现实的敏感捕获都需要依赖于“前理论”的探索勇气。当然,关于“前理论”的探索方式到底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摆脱理论形式的约束——这是哲学,尤其是20世纪之后的哲学一直努力回应的问题。在关于哲学史传统的反思中,海德格尔通过先验论不断地追问事物显现的背景,试图确定思想“被给予”的根基,也由此将哲学的目光引向理解的前见之中,引向关于自我历史性的批判之中。类似的反思也发生在关于“科学发现”的哲学讨论中,“发现”与“发明”、“发现的前后关系”与“证明的前后关系”、“逻辑实证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3]——科学哲学通过构造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别最终都试图澄清,更准确地说是复杂化科学发现中经验要素和理论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科学发现的实质。虽然都是对于理论发现,或者说理论创新的质疑,海德格尔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却是不同的:前者从理论形成的外在背景中,包括历史精神和社会影响方面阐释理论发生的先天条件,后者从科学理论形成的内在角度,包括所继承的范式、所展开的推论等步骤的分析中确定科学发现的本质。但是二者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从经验、范畴或者常识等各种层面的“前理论”状态对于新理论的启发和塑造。他们的观点都从各个角度建立了新理论和“前理论”之间的关联,也因此拆解和弱化了理论创新所被赋予的绝对创造性。
理论的“前理论”
欧陆哲学的先验论和科学哲学的基础论都采取了回顾式的视角呈现新理论诞生的历程。且此视角的广度越大,被吸收纳入到原因和效果的解释之中的因素就越多,原本以专名标注的理论发明也逐渐发散为整个社会的共同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前理论”性的阐释也许正好打开了折叠在理论中的偶然与必然,感性与理性,想象和推理。又或者说,关于“理论”和“前理论”之间的区别恰恰是依赖于两者之间的关联之上。回顾“理论”本身被塑造的历史,就是对此观点的直接支持。从词源构造而言,理论/theory的古希腊语θεωρία由表示所看之物的θεά与表示观看动作的ὁράω共同构成,其本义包含着一种神秘的观看方式:内在于心的观看。根据康福德对于西方思想起源的研究,θεωρία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有一定程度上的多义性,在爱奥尼亚学派中被用以表示出于好奇的观察。不过,这种好奇性观看的目的一旦被授予“命运”“天道”的神秘性,观察本身就会试图在所拥有的视觉中寻找启示性的印记。由此,在俄耳普斯信仰运动中,关于θεωρία的理解必须参考人在祭祀仪式的激发下,透过汹涌的情绪所达到的和世界生命的融合,并于此之中领受“真相”。Θεωρία是在情感激荡中所获得的具有宗教性的先见。
到了毕达哥拉斯的时候,他“重新定义了θεωρία,将其解释为对理性和永恒真理的冷静思考,把生命的路程变成‘追寻智慧’(philosophia)之途。”[4] 毕达哥拉斯净化了θεωρία中原本包含的情感成分,但生命真相仍然作为神秘的信念被保留下来,只不过参与其中的方式由狂欢仪式中所体验的神话故事转换为思维推导中所寻找的和谐比率。真正将θεωρία作为“静观沉思”确定下来的工作最终是通过亚里士多德完成的。“故思辨的哲学(φιλοσοφίαι θεωρητικαί)有三种,数学、物理学和神学……最崇高的知识所研究的应该是那类最崇高的主题。思辨科学比其他学科更受重视,神学比其他思辨科学更受重视。” 作为思辨活动,θεωρία或者展开了推导的步骤,或者保持了内在的直觉,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都最大程度地纯粹化了θεωρία,不仅使其成为纯粹的思辨活动,彻底远离了曾经充满于其中的激荡情感,而且也将“共同性”,换言之“普遍性”作为了思辨活动所应当达到的目标。对于普遍性的最高知识就是对于世界本质的把握。越是追求最高的知识,也就越远离具体的事务和实践,沉浸在关于至善的思考中就是我们所能获得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理论生活”在中世纪被转化为宗教体验中重要的冥思(contemplation)练习,且在中世纪晚期的大学之中,他关于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别也被应用为划分学科专业的基本原则。在这些不多的学科中,以数量和比例和谐为基础的音乐往往被归为纯理论的知识门类之下。然而麻烦的是,在教导和传授关于音阶、音程、和弦等音乐知识时,就不可避免地涉入实践。故而在文艺复兴早期,受到古希腊思想热潮的影响而面世的《音乐学科的理论著作》Theoricum opus musice discipline (1480),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音乐理论》(Theorica musice, 1492)[6],既引入了古希腊音乐理念,同时也包含了具有技术性的计算、对位和测量等实际问题。文本标题使用的theoria暗示了关于主题的系统性研究和说明的内涵,为当时所流行的文本标题,如专著/opus,方法/methodis,评论/commentaria等等增添了一种新的选择。
随着对于理论实践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纯粹思辨”的崇高性也越来越受到批评。作为对于亚氏经典逻辑理论《工具论》的批评,培根在1620年完成的《新工具》中表达了他要重塑求知道路的志向,要求自然哲学能够同时吸纳思辨知识和实践知识。更准确地说,是要求在从具体的对象到普遍性秩序的逐级上升中,对自然的解释应当具有确切的推导性。为了解释可能发生在认识中的心灵误导,培根特别举出了几种假象,其中的“剧场假象”(idola theatri)中的“剧场”和“理论”共享了同一个词根θεά/观看,且都是出于人内在的想象。而关于此假象,培根如此描述:“一切公认的学说体系只不过是许多舞台戏剧,表现着人们自己依照虚构的布景的式样而创造出来的一些世界”。[7] 纯粹思辨的知识所产生的世界秩序,就和人们在剧场中编造的演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二者都更倾向于合乎内在逻辑的现象,而避开了相反的事例;都更容易受到人的情绪和意志的牵引,而让理性困于学说体系的假象(idola theoriarum)。克服意志误导和感性偏差的方法,对于培根而言,就是要借助于工具和机器推进实验研究,在精微的观察中建立原理。以实验生产理论的方式,在牛顿的哲学中被施以更严格的要求。在第二版《原理》的最后部分,牛顿拒绝了无法证明的“假说”:“因为凡是不能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都必须称为假说;而假说,不论是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的,不论是基于神秘的品质还是机械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地位。在这种实验哲学中,命题是从现象中推导出来的,并通过归纳法使之成为一般。”[8] 排除情绪与意志,排除想象与臆断,才能更严密地推理,并且依照实验确定法则和定律。培根与牛顿对于理论的要求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然而,如此回望此概念,关于理论的理解越来越世俗化,参与理论的方式也从神秘而有等级的有限世界逐渐置换为心灵无限的理解力,形成理论的过程也越来越排斥感性和精神性,越来越强调客观性和自足性。相应地,理论所要解释的方式也从以秩序性整体为前提去观察具体对象,而发展为从具体对象出发,通过定律、法则,逐渐衍生出漫无边际但又被同一性贯穿的宇宙。
我们所提出的“前理论”正是针对于启蒙运动之后的“理论”形态而言,尤其是针对于“理论”通过实验而获得的自我确信。即使是在启蒙运动的核心时代,也已经存在了很多怀疑以客观性、实证性为标准的理论。作为博物学家,布封这样论述自然史的研究结果:“造物主的手好像并不是张开来送给我们人类一定数量的物种,它似乎同时地把一个相关的和不相关的生物世界提供给了我们,把一个无穷无尽的、和谐的和矛盾的组合,和一个永无止境的毁灭与再生提供给了我们……最睿智的头脑和最博大的才智也永远达不到这种认识高度,因为最初始的那些原因我们永难得知,而那些原因的总的结果也像原因一样让我们实难明了。”[9] 精微的工具可以帮助研究者撬开对象的内部,观察到眼力所不及的现象,但是,若要实现关于世界的根本性理解,纵然人的理解力本身无法穷尽世界的原因,工具的帮助对此却也不仅没有必要,反而会带来一叶障目的片面性。布封的博物志试图跨越物种的分类,在自然的历史中溶入无序、异质,不断地挑战所形成的知识体系。那么从这个角度上重新看待法国哲学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调动和借用就会有新一重的意义:他们并不是要利用其他门类的知识为自己的观点做辩护,而是在根本上就并不认同知识分类的方法,不认同理论所被指派的工具属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理论之中保留无根据的假说,以此保留自由的猜测、天真的想象,保留哲学在存在面前的惊讶,保留人在经验之中心领神会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法国哲学的理论内部要保持“前理论”的思考姿态。
当代法国哲学中的“前理论”
对于“理论”内涵的历史性追溯启发着我们理解“前理论”被提出的依据。在当代法国哲学的内部,巴什拉、福柯、德里达等人通过反思和批评哲学当下的思维方式,显明了各自所构造的哲学的“前理论”思考方式。我们选取列维纳斯和德勒兹作为代表,尝试理解他们在“前理论”式思考之中所分别实现的认识论和历史论的突破。
作为列维纳斯最核心的著作,《总体与无限》提出了两种哲学,一种是以现象学,尤其是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为代表的总体哲学,另一种是抵抗总体化的无限哲学。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包括海德格尔追求的存在本质,都试图通过不断地过滤感性以便将世界总体化,将复多归于一,将沉思归于体系。列维纳斯称此为西方哲学中对于总体的乡愁:“在精神性的东西(le spirituel)和有意义的东西(le sensé)永远都在于认知的西方哲学中,这种对总体的乡愁触目皆是。就好像:总体已然被失落,且这种失落不啻为精神之罪孽。如此一来,对现实的全景式观看(vision)才是真理,才能使精神满足。”[10] 全景式观看(la vision panoramique) [11] 不仅预设了观看者将自身置于被观看对象之外——更确切地说是“之上”,而且观看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预期和意愿要求对象表现出可被理解的特征,以便于他将这些特征关联为包含全部的总体。故而,隐藏于总体性哲学核心之处的,仍然是绝对的主体,是褫夺他者存在的绝对自我,也因此是自我封闭的思维方式。既然总体性哲学的策略包括还原的方法,本质性的真理,以及最后要达到的存在的整体性和经验的纯粹性,那么,相应地,对抗此总体话哲学的方法就包括了承认并表达存在者之间的复多和异质,以无限的创造溢出总体性哲学所预设的“同一性”。“关键在于用抵抗着综合的分离观念代替总体观念……肯定那凭借着创造的从无造有,就是质疑在永恒内存在着万物的预备性共同体(la communauté préable)。”[12] 分离就是从总体中的出走与逃离,正如家宅提供了从公开袒露状态中的暴力出口,列维纳斯通过探讨居家“享受”(jouissance) 之中主体的心理状态,以及主体和对象的关系,既溢出了胡塞尔的意识结构,也越过了现象学在认识论基础上为主客体构造的支配关系。如果感性经验的内在厚度足以抵抗理论同一性的透视,那么凭此人类主体就应该可以将自己肯定为无限的存在者,而且通过自我的创造活动切实地展开其生命的无限性。进行创造才能实现分离。
这个时代给予了创造最高的价值,期待着从创造中打开新的可能性,从而超越当下的生存方式。如此理解创造必然不能摆脱主体性,因为创造往往被作为主体性的表达,尤其是海德格尔将此作为主体的最强表达。如此理解创造主体回避着内在的不安:如果将创造归于主体,那么就需要从主体的角度理解创造的意义和依据,而这又会导致将创造重新拉回到秩序的连续性之中,就又难免回到前文已经提到的“理论”和“前理论”的循环性论证中。对于创造的起源和主体的形成,列维纳斯提出了“无端(an-archie)”,并将其置放在“端始(arhie)”之外,或者说跳出关于“秩序”和“无序”——秩序构造的本体论根基之外:“无端止住本体论的游戏,而这一游戏正是意识,在其中存在迷失自己、再找回自己,并照亮自己。”[13] 无端并不与秩序相对,而是与开端,也就是始源相对,无端就是对于这种历史性思维的拒绝。作为历史性思维的典范,黑格尔的辩证法呈现了意识如何主动赋予存在以意义的游戏。而无端却是被动性之无端,创造也是应承性的自我辩护,是自我在他者面前为自身的分离性所作的辩护。列维纳斯将他者置放在自我面前,并以此作为主体形成的条件,也就是提出关于主体性的新的安置方式:“因此本书(《总体与无限》,笔者注)将表现为对主体性的保卫,但它将不在其对总体的单纯自我主义的抗议的层次上来理解主体性,也不在主体性面临死亡时的焦虑中来理解主体性,而是把它理解为奠基在无限观念中的主体性。”[14] 无限观念并不只是、也不首先表示存在论层面中的无限,即无限的多、无限的丰富,而是对于封闭性、确定性的否定和超越。无限观念中的主体超越了身份逻辑中的主体,其超越的方式就是显露出主体包含了比可识别、被规定的身份更多更复杂的内容。
列维纳斯一方面从自我的内部发出的身体和灵魂交互作用的追问,另一方面从自我的外在性展开的自我和他者所处关系的探讨,他在对西方的主体概念表示出最强烈的质疑的同时,也试图将此概念,以及在此概念之下所衍生的理论模式重新引回人文主义的发展路径中:“事实是,今天人文科学的崛起是世界之光变化的结果,是某些意义失去效用的结果。在关于人的理解中,对逻辑形式主义和数学结构的乡愁超越了方法论的谨慎和技巧,同样也在物理学中超越了对数字和测量原型的实证主义模仿。在人的秩序中,这份乡愁也更中意于可从外部识别的数学身份,而非自我与自我的偶合,甚至一百年前,人们就想据此锚定精确知识的方舟。从此以后,主体从理性的秩序中被消除了。”[15] 原本出于认识的自由所引发的不再是由人的创造力成就世界,而是通过由思想生产的真理去抓握和定义人的存在。为了满足真理的丈量方式,自我离弃所拥有的内在性,“无褶皱亦无秘密地溶入整体。人的整体都是在外的。”[16] 。这种在外的状态是指个体暴露在外的状态,是个体失去居所、失去家庭时所陷入的孤立隔绝的无助状态,也是被连根拔起、一无所有的贫乏状态。理论对于人的占有越是严苛,也就越是显出暴力承受者的被动和屈从,显示出“我”置身在概念、逻辑、数列——概念秩序下的脆弱性。然而更深的被动性却通过人对于自我感性的主动离弃揭示出来,同时,更深的脆弱性也滞留于难以摆脱的创伤阴影、不能抚平的身体褶皱之中。那么人文主义的责任正是要不断地进入人生存的被动性和脆弱性,通过为被剥夺了存在的在场者辩护,化解同一性的强制力。“观看(θεωρία)”存在的无端和无限,这既是回答第一哲学问题的方式,也是和“前理论”相遇的方式。
在列维纳斯所提出的被动性的一侧,德勒兹对于哲学使命的理解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到达“前理论”的路径。在他晚年和迦塔利共同完成的《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提出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e)的哲学观。简单地说,他认为相比于其他的学科,哲学的任务就是创造概念。这种创造论首先表示否定哲学史预设的思想的连续性,其次是拒绝承认任何普世性的原则。因为普世性、总体性的概念对于解释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效力有限,并且反过来,为了能和当下的处境相结合,人们反而还要解释那些脱节的概念。也就是说,为了解释当下、为了在当下解释抽象的概念,新的概念必须被创造。哲学的事业以概念的创造为起点,然后要展开由概念所辐射出的内在性平面,再培育出具有某种思考风格的概念性人物,最终到达思想所建立的领域、所构造的共同生活方式——从个别的点,逐渐聚集为视域,到多个视域的转换和汇集,再到最终这些杂多可能融合表达为的民族、国家或者时代。德勒兹的建构主义的方法回应了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构造逻辑:从简单到复杂,从纯粹到综合,从个体到集体。不过,德勒兹对于创造的理解仍然不同于列维纳斯所提出通过纯粹的无中生有而达到的“无限的无限化”的效果。在德勒兹看来,概念的创造已经预设了思想在存在之上巡视的方向和速度,而思维的方式同时也预设了某种风格和姿态,包括相应的精神氛围的想象、生活世界的样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哲学作为概念的创造也总是预设着“前哲学”的(Pré-philosophique)思考:“前哲学丝毫不意味着事先存在,而是指某种并非存在于哲学以外的东西,尽管哲学预设这个东西的存在。这些都是哲学的内部条件。”[17] 正如哲学预设着“前哲学”,理论也以相似的方式包含着“前理论”性的直觉。或者说,每一个被创造的概念都内含着一幅思维的图景,也对应着一种生命的情态。并且正是对于生命的本质直观,激发着思想进行概念的创造、内在平面的建构、概念性人物的塑造。德勒兹以此将哲学概念,包括组成概念的理论从抽象性、逻辑性、普遍性的空中楼阁中释放出来,重新恢复它们与创造冲动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得思想的光芒重新绽放:“我们从未涉及构成思想的真正力量,从未把思想本身同它作为思想所预设的真正力量,把真理同真理所预设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是,没有一种真理在成为真理之前不是某种意义或价值的实现。真理作为一个概念完全是不确定的。一切都取决于思考内容的意义与价值。”[18] 在这个意义上,“前哲学”对于“哲学”而言,构成了后者所预设的理解力以及所要实现的论证目标。那么哲学所要追求的就并不是纯粹的理论,而是要获得建构思想的能力,在概念的支点下凝聚其“非哲学”内核,在思想的图景中展开“前理论”起源。
概念和思维图景的亲缘关系,映照出创造行动在现实世界中所投下的具体真理与特殊价值,这也是概念必须包含的“前理论”维度。而从另一个角度上理解,当概念脱离了其所思考的内容,就会失去曾经拥有的直观性和洞察力,而成为庸常的定见(opinion) 。哲学和定见的斗争由来已久。从苏格拉底的对话到胡塞尔的悬置方法,哲学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跳出定见的窠臼。然而,若因此将哲学的使命设定为日常批判,则会陷入空虚的自我感伤之中。“概念一旦被放入一个新环境,批评充其量也只是为了证明某个概念已经烟消云散,丧失或者获得了某些改变它的组成成分。可是,那些只评论不创造的人,那些只满足于捍卫消亡了的概念而不懂得赋予它起死回生之力的人,他们是哲学的伤口。”[19] 伤口让我们感知到痛苦,但却不带来任何的行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德勒兹认为批评过时的概念,固然显示出其效力的衰微和贫乏,但仍然是守在旧的逻辑和秩序之中,思想并没有由此获得创造的起点。既然概念和其所属的思想领土关系如此紧密,创造性首先就意味着离别故土、弃绝思想的条件、毁灭所有的规范。概念的创造首先排除所有给定的条件和导向,拒绝思维的自然状态。无前提的思考方式,既没有任何概念可以借力,也没有确定所思的对象和内容。思想自我剥夺了惯常的效力和功能,以一无所知、无所凭借的方式尝试接近原初的经验、纯粹的混沌。因此,与其将哲学的建构主义理解为从无到有的创造,也就是以个人的创造之力所逐渐建立的思想版图和精神领地,不如将此创造理解为主动摆脱定见的塑造,在现实秩序中引入混沌从而激起思想的行动。“在思想之中激起了种种不归属于认知的力量,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亦不属于明天,它们完全是另一种范型的强力,它们处于一片永远无法被认知,永远不能去认知的terra incognita[未知领域]之中。”[20] 由概念逐渐发散、铺展成的思想领地,无论其理论的跨度是多么大,其巡视的范围是多么广,其所有的领地都始终被纯粹的经验所包围。思想生产的秩序空间即使占据整个大陆也仍然被未分化的汪洋所环绕,那么创造就像是远离大陆、毫无目标的航海探险,要穿过“前理论”的模糊和动荡,重新完成对于混沌的征服和对于世界的再造。
在德勒兹所提出的通过创造概念而创造哲学的路径中,他拒绝所有对于思想的预设,甚至拒绝包括自然权利、生活世界、思想的基底等等原信念。在他看来,所有的信念都源自思想本身的构造,所体现的是曾经发生的思想效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他哲学中所包含的“前理论”阶段,就是为了摆脱定见的束缚和传统的负担,为了追求思维的无限性。而这种无限性,对于德勒兹而言就是不将自身交给任何理念,自觉抵制超验性的幻象。对于哲学的期待最终被总结为作为绝对的内在性:“绝对的内在性是自在的:它不存于某物也不据于某物,它既不依于客体也不属于主体。”[21] 依于自身而在,出于自身而动——德勒兹用内在性描述思想的内在自由和外在无限,同时也是在描述纯粹生命的状态,超越于任何属性从而只能以“不定冠词”去指称的生命状态。这也是德勒兹在哲学工作中所追求的目标——跨越所有界限、不成为任何特殊理论的“前理论”的思考方式。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的“前理论”
列维纳斯和德勒兹所铺设的“前理论”的路径,尽管在此之中他们所阐释的“无限”的内涵、“创造”的目的,以及“超越”的界限各有不同,然而他们却都在尝试通过诠释概念间的矛盾、感觉中的独特,进而打破理论笼罩之下世界趋向同质、归于和谐、沉入平静的假象,也在探索穿过理论隔层接近纯粹经验的路径。更广泛地看,列维纳斯和德勒兹从不同的角度上反映出当代法国哲学对于理论阻碍经验和认识的警惕,当然在更深的层面上,是他们对于生命自然状态的好奇和惊讶。不管他们对于生命所持的理解如何,或者是外在与内在的相争,或者是生命力的冲突与汇聚,或是权力和真理的书写对象,完全不同于科学所要求的客观立场,他们被这一哲学命题所吸引,并且为了避开已有理论的障碍,力争展开无前提的推理,“前理论”的状态就成了他们的论证策略。这就像福柯对于自己研究的描述:“不是把历史用作批判方法来拷问普遍概念,而是从普遍概念不存在这个论断出发,来询问我们可以书写什么样的历史?”[22] 福柯从具体实践出发,更准确地说他寻找着普遍概念在现实中的着陆点,并依此检测出概念的效果。而此检测方式本身就已经暗含了福柯对于现实的模糊构造,以及关于生命的“前理论”领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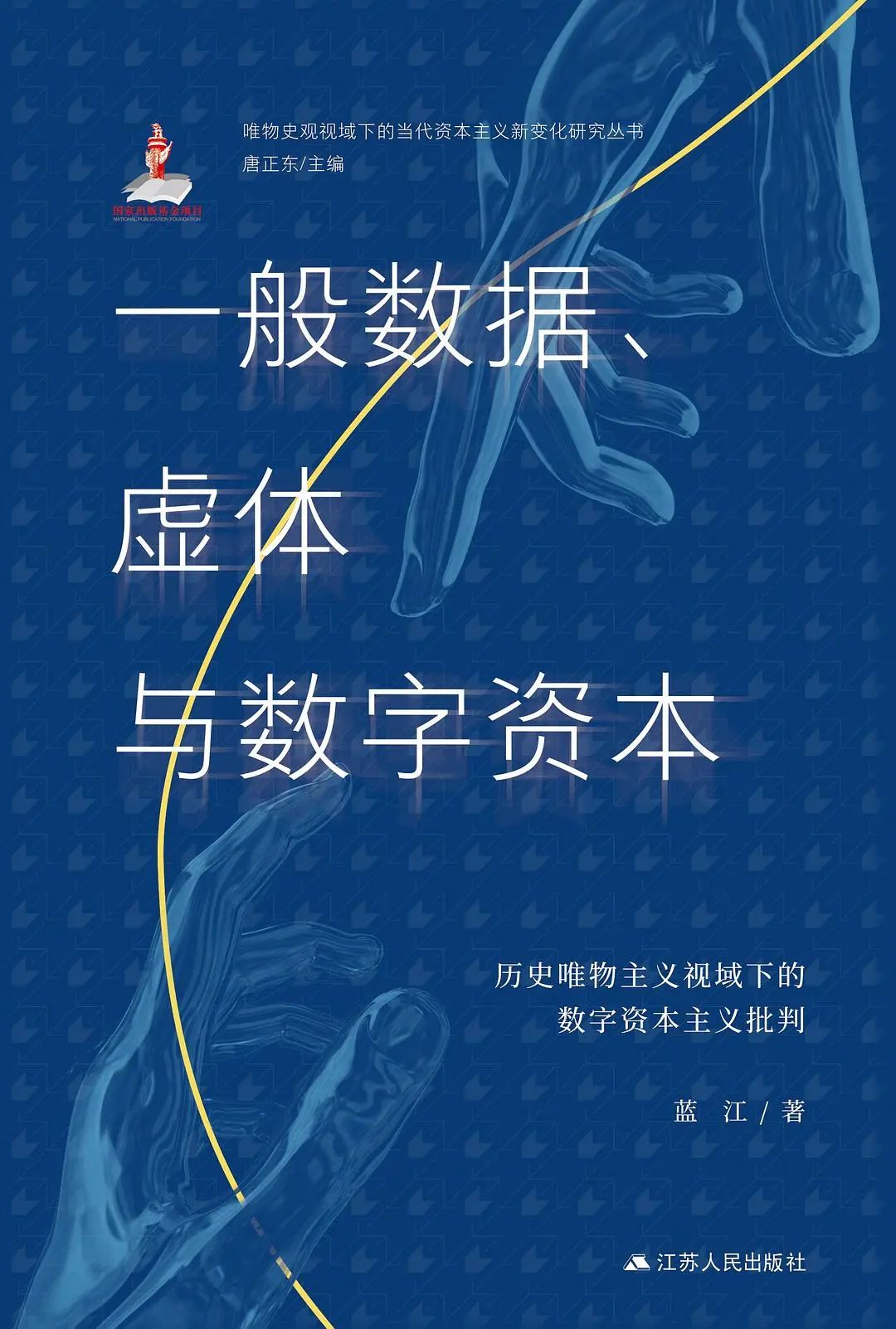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法国哲学的“前理论”态度释放了思想构造的自由,扩展了学术关注的对象。在萨特、列维纳斯和福柯等人的哲学理想中,思想所追求的目的地从图书馆迁移到居所内外、街头巷尾,所关注的对象也从书桌上的墨水瓶转移到了咖啡馆里的酒杯或者监狱中的囚徒。相比而言,我们当下的生存境况发生了更深刻也更迅疾的转变,哲学研究也尝试揭示秩序表面之下的紊乱,构造新的思想平面,以理论的光芒照亮动荡的局部。而蓝江新近完成的《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以下简称《数字资本》)所尝试实现的正是这一哲学目标。作者在后记中指出我们目前现有的哲学理论不再能够透彻地勾勒当下的发生,也不再能够有效地反映社会运转的节奏。“我们不能直接套用那些传统思想家的结论……尽管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可以为我们提供反思当下社会现实的理论渊源,但是,对这些最直接的现实的哲学反思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23] 在对于现实本身的认识中,作者尽管坚持了批判哲学的传统,然而却以广阔的社会背景和理论视野,充分调动新近的研究成果,最终为当下生存的状况做了诊断:“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必须面对的社会现实,那么我们的社会现实就是数字化社会和数字资本日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在全球范围内,数字资本主义正在取代以往的产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衍生出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理论认识。”[24] 为了构造新的资本生产逻辑,作者提出了三个最基本的概念,即“一般数据”“虚体”和“数字资本”。尽管通过一种对立性的区别关系,所提出的这三个概念从马克思哲学中“一般智力”“实体”和“货币资本”演化而来,然而作者却借助这三个概念重置了生产与消费、真实与虚构、自然和异化的阐释逻辑,绕过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证模式,也绕开了法国批判理论中关于商品生产和欲望流动的论证模式,剖开网络世界和物质实存之间的融合和间隔,阐释数据组合为虚体进而构成自我增殖的新方式,也就是数字资本前行的动力之源。最为重要的是,作者在陈述商品生产的新形态的同时,不断地引入生命档案、人口统计、算法治理、控制技术等政治学的概念,以及以对象为导向的新本体论,在存在向度的无限关联中逐渐叠加出现代社会的庞大复杂、万物相生的机器形态。
就论证的方法而言,《数字资本》也体现出法国哲学中的“前理论”的写作特征。以电影《健忘村》作为开篇,以华为的操作系统“鸿蒙”所预言的5G作为结尾,于两端之间,马克思、海德格尔、卢卡奇、福柯、塞尔、阿甘本等思想家谨慎地穿行在DNA信息库、手机APP、文学小说、人工智能、当代电影作品、新兴的网络游戏这些既无实体但又无比真实的数字生活形式之中。数字化主导之下,“资本”“此在”“物化”“人口”“拟-对象”“装置”等概念的确还能在某个层面上发挥解释的效力,并提供观察的支点,但除了“数字化”这个基础性事实之外,我们还没有获得任何一种本质的判断,亦未能充满自信地面对当下的生存境遇。更糟糕的是,“在这个历史趋势之下,个体实际上没有太多选择,我们在更多时候是被强行拽入到这个进步轨道上的,没有其他选择!”[25] 尽管数字化中的所有产品都出自于人的智慧,并且越来越深地渗入到精神活动和物质存在之中,然而人们却越来越感到被自己的发明物所控制、操纵,沮丧于主动性的丧失,进而提出了关于技术和技术使用方式的批评。然而,如果更进一步地拷问这种被动性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面对当下的技术发明,尤其是面对数字技术的发明,绝大部分人都是作为技术的最末端,也就是作为使用者被动地承受发明的结果。具有突破性的是,《数字资本》又更进一步地指出,技术的发明并没有自我终结于使用,而是在被使用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和不同的人相连接的杂多境遇中,重新开始技术的学习和创造。不同于一般技术批判理论的消极态度,《数字资本》乐观地畅想技术的未来:“在计算和学习能力得到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面前,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有朝一日,如此庞大的信息和数据量,如此复杂的调节和分配运算,可以在人工智能的统筹计划下完成。而且,人工智能也不会具有道德上的问题,即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人工智能拥有自利的意识,从而在资源和生产的调节与分配上为满足个人的私利,而让计划陷于腐败和不公正。”[26] 自私自利、腐败不公——这些结果的原因既然在于人本身,那么技术的异质性恰好在克服人性的尝试中提供了一种值得期待的机会。而之所以值得期待正在于技术总是在超出期待的意外中来临,在理论的虚弱之中显现。
最后,就论证所完成的结论而言,《数字资本》从当下生活表面的快速流动中,相对完整地捕捞起现代性在我们身边显露出来的独特现象。电影小说、百度谷歌、淘宝天猫、微博朋友圈、富士康生产线、英雄联盟、刑事侦查等等各种现象都成为作者讨论和分析的对象。在每一样东西上所投下的理性之光——以这种方式继承了布封在自然研究中的启蒙精神,但又远离了启蒙理性对于体系化知识的追求。作者呈现了网络技术下衍生出的数字资本在生产、交往、治理、认知等各个层面所引发的不同程度的振动,尽管这些振动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发生共振,但它们却从根本上破碎了将存在作为整体进行把握的可能性:作为整体性的世界遁去了,随之遁去的还包括曾经的秩序性、等级性和稳固的价值体系——而如果这些构成了封闭性的有限总体的话,那么它们的遁去则表示着动荡失序的、不确定的开放世界的降临,对于断裂和多样的事实性承受。尽管在局部的范围内,认识的工作仍然保留了构造关联、解释原因的可能,但是由此所构成的可理解的网络关系,既然失去了本体论的基础,也必然在不同的层面中被分解、替换或者取代。换言之,理论的构造本身不得不处于流动性和脆弱性的前理论状态。《数字资本》在最模糊的意义上,呈现了社会作为机器的总体性存在,然而在机器不断地自我增殖的趋势下,能了解这台庞然大物进而驾驭它的可能性却越来越低,也越来越短暂。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资本》依据于人的有限性,怀疑主体治理本身合理性的根基,从而更倾向于支持技术的竞争,借助机器的加速运转,淘汰过时的观念,冲破管理的局限。在《数字资本》对于人和秩序的怀疑和法国哲学对于体系性理论的质疑之间,发生着深层的共鸣。尽管这份怀疑的态度完全不能确定哲学在未来时代的命运,但是能够确定的是,哲学要坚持“前理论”的姿态。这或许可以理解为面对人复杂的存在现状,哲学仍然坚持的求知决心和自省勇气。(文/李科林,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萨特访谈参见电影字幕记录:Sartre, Un film réalisé par Alexandre Astruc et Michel Contat, Texte intégral, Pais: Gallimard, 1977, pp. 39-40,波伏娃回忆参见:Simone de Beauvoir. La force de l’âge, Paris: Gallimard, 1960, pp. 157-158.
[2] 阿兰•巴迪欧,让-吕克•南希,《德国哲学谈话录》,扬•沃尔克编,蓝江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1年,第13页。
[3] 参见卡尔·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Hans Reichenbach, Expereince and Prediction. An Analysisi of the Foundations and the Structure of Knowledge, Chicago: Univeristy of Chicago Press,1938.
[4] 康福德,《从宗教到哲学:西方思想起源研究》,曾琼、王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203-204页。
[5] Aristotle,Aristotle’s Metaphysics, Volume I, a revised text with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ary by W.D. Ro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4, 1026a 20-25。译文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
[6] Franchino Gaffurio,Theoricum opus musice discipline,Napoli:Francesco id Dino,8 October 1480;Theorica musice,Milano:Filippo Mantegazza,impensal Io.Petri de Lomatio,15 December,1492.转引自:杨·赫林格,“中世纪的测弦学”,《剑桥西方音乐理论发展史》,托马斯·克里斯坦森编,任达敏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1年,第159页。
[7] 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1页。
[8] Isaac Newton,The Principia: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ional Philosophy,a new translation by I.Bernard Cohen and Anne Whitma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943.关于假说/hypothesis在牛顿文本中内涵的变化,可参考:科瓦雷,《牛顿研究》,张卜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7-52页。
[9] 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De la manière d’étudier et de traiter l’Histoire Naturelle”,Histoire naturelle,générale et particuliére.Tome 1,L’imprimerie Royale,1749,pp.11-12.译文见:布封,《自然史》,陈筱卿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页
[10] E.Levinas, Éthique et Infini: Dialogues avec Philippe Nemo, Paris: Libraire Arthème Fayard,1982, pp.80-81, 译文见: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王士盛译,王恒校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4页。
[11] E.Levinas,Éthique et Infini:Dialogues avec Philippe Nemo,Paris:Libraire Arthème Fayard,1982,pp.80-81
[12] E.Levinas,Totalitéet Infini:essai sur l’Extériorité,Kluwer Academic,1971,p.326. 译文见: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4页。
[13] E.Levinas,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de l'essence,Kluwer Academic,1978,p.160.
[14] E.Levinas,Totalitéet Infini:essai sur l’Extériorité,p.11.译文见: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前言第7页。
[15] E.Levinas,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Paris:Fata Morgana,2017,p.96
[16] E.Levinas,Humanisme de l’autre homme,p.97.
[17] 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LesÉditions de Minuit,1991, p.43,译文见: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55页。
[18] Gilles Deleuze,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3,p.118.译文参见:德勒兹,《尼采与哲学》,周颖,刘玉宇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21-222页。
[19] Gilles Deleuze,Félix Guattari,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p.33.译文见: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第238页。
[20] Gilles Deleuze,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3,p.177.译文见: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安靖,张子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
[21] G.Deleuze,«L’immanence:une vie...»,Deux régimes de fous:textes et entretiens 1975-1995,édition préparée par David Lapoujad,Paris:Leséditions de minuit,2003,p.360.
[22] Michel Fourcault,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Cours au collège de France(1978-1979),Gallimard et Seuil,2004,p.5.译文见: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法兰西学院演讲系列,1978-1979》,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23]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2页。
[24]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主义》,第271-272页。
[25]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主义》,第209页。
[26] 蓝江,《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主义》,第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