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人书法”研究的开山之作:《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出版 。沈曾植为清晚期学术通人,其书学理论、书法造诣在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2022年为沈氏逝世100周年,王谦著《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近日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通人书法”和“寐草”是此书的两个关键词,作品主要创新也由此体现。其一,首次提出“通人书法”的概念,以沈曾植为近代“通人书家”之典型,对其诗学、诗功和书学、书艺进行研究。作品从“学人之诗”入手,聚焦于沈氏晚年书风的形成轨迹与定型范式,探讨其书学理论、书法成就与学术之间的多重回互关系,作者的分析和立论基本不离“通人”层面,知人论世,沈曾植书法研究由此而进入新的阶段。其二,作者借鉴当代学者将王蘧常章草命名“蘧草”的理路,将沈曾植(号寐叟)晚年书风定名为“寐草”,借此厘清书法界多年存在的书体混淆,并将“寐草”视为对王献之所倡导的在“稿、行之间”“改体”主张遥隔1500年之后的首次成功实践。作者认为,沈曾植以其并不完全遵循章草规范的寐草,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开放范式,昭示出书法创新的无尽可能性,这种贡献历久而弥新,对当代书法创作亦具启发价值。
此外,作者的贡献还体现为文本解读方面的正本清源。对书法理论界影响较广而与沈曾植其书、其学并不相符的观点,如沈氏“晚年主要师法黄道周”,沈氏主张并实践“古今杂形,异体同势”等等,均作出理据充分的辨驳。
著名美术理论家、书法家李一先生认为:“此著作以‘通人之学’与‘通人之书’为主线,围绕一显一隐两个主题展开。显者为沈曾植书法研究,隐者则是中国历世相传的‘通人书法’传统。显性主题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隐性主题大处勾勒,处处可见,两者彼此融通,互为表里,显隐交织,斐然成章,具见作者的历史考据功力与学术思想深度。”
著名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叶培贵先生认为:“作者将沈氏之书这一个案研究拓展为整个中国书法统绪的重新梳理,事实上‘重构’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乃至价值体系。扎实的文史功夫,使作者的解读常常能够超越书法本身而深入文化的深处。其精彩处,尤其集中在第二章《书学理论》。作者的文献解读能力,保证了本书真正具备了追问沈氏思想精粹的可能性。”
本书作者王谦现为山东艺术学院教授。全书40万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曾获得首届“中国传统文化民生奖学金·沈鹏奖学金”特等奖,并同时入选人民美术出版社“人美学术出版基金”和“人美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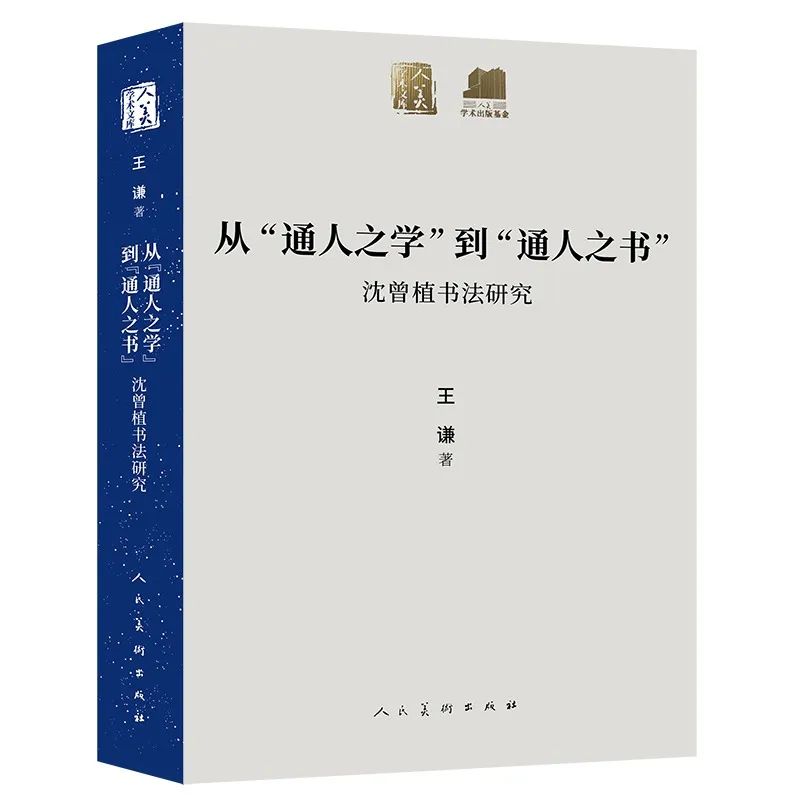
【书名】: 从“通人之学” 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
【作者】: 王谦
【ISBN】:9787102086132
【出版社】: 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03
【定价】:98元
目录
序一 李一3
序二 叶培贵7
绪论两个主题的交织与融合1
第一章 从通人之学到学人之诗9
第一节 一生行迹10
第二节 晚清背景下的通人之学29
第三节 诗学与诗功56
第二章 书学理论87
第一节 晚清书法变局88
第二节沈曾植书学概况与书论特色114
第三节 碑帖研究151
第四节 书法研究174
第五节 书学主张193
第三章 书法造诣213
第一节 书风嬗变分期214
第二节 寐草名实辨析253
第三节 寐草形成元素分析269
第四节 寐草之范式315
第四章 沈曾植的地位暨通人书法的意义373
第一节 沈曾植书法的历史地位375
第二节 沈曾植与近代以来章草复兴383
第三节 沈曾植之后的碑帖融合403
第四节 通人书法的概念与意义410
结语431
主要参考书目441
附一 沈曾植研究百年概说453
附二《寐草行》475
后记479
走进通人的世界
——《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序
日前见到老友刘绍刚一篇谈读书写作的杂感,说及治学术者读书面要宽,不宜自我限制在单一的领域内。一个学人如果除了专业书其他的都不读,那这个所谓专业也很难做出名堂来。如绍刚兄所言,目前不少学人已走上狭窄的道路,阅读、写作只作为维持生计的手段,“著书都为稻梁谋”,毛驴拉磨般围着自己的专业团团转,流风所被,连一些在读的博士生也早早濡染此习。多年置身美术学和书法专业的实践与教学工作,此类现象我见得不少,因而深有同感。当然,世事总有例外,王谦的状况就与一般人颇为不同。
王谦曾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年龄仅小我八岁,论起资历,我们当是同辈人。他出道较早,来读博士之前,已具备正高职称,早就是个有着多年工作经验的资深编辑和著述甚丰的作家了。上世纪80年代,王谦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山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30年间,他担任责编的图书达数百本,自己也出版了20余部著述。编读相兼的阅历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得以多方涉猎,文思泉涌。王谦天赋很高,思维敏捷,古今中外文史哲艺无不涉笔成趣,才思旁注,甚至连足球评论等也写得扎实老到,令人赞佩。他的书很受欢迎,我和许多朋友原来都是他的读者。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早已衣食无忧、看来前程似锦的王谦却下决心改变人生方向,毅然放弃原有的一切,投考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且一而再再而三,不弃不馁地连考了三年。
进院学习时王谦已逾知命之年,此前我劝过他不必另起炉灶到考场上和年轻人竞争,他认真地告诉我,投考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今后会将精力转到书法上来,争取在这方面做点事。至于年龄更不是问题,“活到老,学到老”,现代社会知识更新换代迅速,每个人随时都在学习之中。王谦刚入校时,我曾担心他年龄略长,无法与小二三十岁的年轻同学一起住集体宿舍。事实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多余,他不单适应了集体宿舍的生活,而且还深以和小同学相处为乐。他与大家在宿舍里交流思想,讨论学术,共同泼墨挥毫,意兴勃发,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与王谦同住一室者曾形容他是“六〇后的年龄,九〇后的心态”,并告诉我,王谦每天睡不到四小时,早早就起床读书,精力比青年学子还旺盛。我与王谦相处也有这种感觉,一谈到学术问题,他就兴致高涨,滔滔不绝,整个人都焕发出少有的活力。我在一边听着也深受感染,仿佛自己也随之年轻了许多。
出生于书画之家的王谦自幼即受家学薰陶,自记事起即对书画产生兴趣。从第一次拿起毛笔到正式入行攻读书法研究博士生,中间隔着半世纪,所以王谦自己笑称是“草蛇灰线,伏脉五十年”。五十年的伏脉造成了他深厚的知识积累、宽广的学术视野,为他的书法研究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基础。一旦走上专业之路,这伏脉的作用立时显现,王谦厚积薄发,一发而不可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连续发表论文十多篇;撰写四十万字博士论文的同时,完成了一部与论文密切相关的《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也是四十万字,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而他认真推敲后结撰而成的《平复帖考证》就书法史名作提出个人见解,尤其令人耳目一新。
研究沈曾植书法的博士论文,选题是我们共同商定的,其后王谦广采博收,深思细考,最终独立完成,答辩后受到各方的好评。之所以选沈曾植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沈氏在近代书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称得起是现代章草的不祧之祖。沈曾植学识精深,博学多通,在经史、文字、音韵、训诂、诗法、律令、舆地等方面都有突出贡献。其书法与古为新,开创了碑学章草一途,经他的学生王蘧常等传承发扬,形成现代章草的新面目,传播开来,蔚然成风。面对这样的通人大儒,研究者若无足够的文化积累和多维立体的逻辑思维能力,在搜罗和把握史料基础上全面、立体、系统地了解其人、其学与其书的关系,恐难胜任这一艰巨的学术任务。确定选题时,我预感到以王谦的学术基础和生命状态,完全有可能走进沈曾植的内心世界,与往圣前哲展开充满睿智的深刻对话。结果证明,他确不负所期。
论文脱稿后,王谦坦言,回看已有成果,感觉到一种呕心沥血的畅快。读完全篇,我深切体会到,这次写作对于王谦来说,不啻一场全身心投入、义无反顾的修炼,他在废寝忘食的钻研中逐渐突破成说、突破自我,实现了个人学术乃至生命的飞跃。整个研究以“通人之学”与“通人之书”为主线,围绕一显一隐两个主题展开。显者为沈曾植书法研究,包括书学理论、创作实践两方面,而以沈氏晚年典型书风为重点,隐者则是中国历世相传的“通人书法”传统。显性主题条分缕析,层层深入;隐性主题大处勾勒,处处可见,两者彼此融通,互为表里,显隐交织,斐然成章,具见作者的历史考据功力与学术思想深度。通篇由点到面,由平面到立体,史论述评与图像分析有机结合,引领读者一步步走进沈曾植的世界,看到了中国书法、中国文化的瑰奇绚烂、博大精深。
教学相长,王谦的学术研究也带给我很多启示。论述沈氏碑帖题跋时,他发现了大学者钱仲联先生的一些误读,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考证《平复帖》相关问题时,他在全面研究文本及史料的基础上,就《平复帖》的文体、作者、文字释读、书体归属等提出了异于启功先生的新观点。这种坚持独立思考、反对人云亦云的态度,是所有人文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要真正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落实到我们的学术工作中,让研究领域出现更丰硕、更有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王谦其勉之。(李一 2020年4月28日于美利坚西海岸)

王谦《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序
中国书法,作为目前属于“艺术”大类下“美术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在当代经过了特别的历程。许多中国传统学问,都先于中国书法而经过这种历程,比如中国画,也同属美术学下的“特设二级学科”。“特设”,从字面上已经昭示了其内在难以直言的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学科”之名以及体系,是舶来品。相比于绘画,完全为西方所无的中国书法,获得这一名称、进入这一体系,过程十分曲折。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并不承认中国书法是一种艺术。至少在体制的层面上,一直到1981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书法作为一个艺术门类,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而在教育体系内成为“学科”,则是创下筚路蓝缕之功的上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末浙江美术学院(率先开办本科和硕士)和90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率先培养博士)的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和欧阳中石等先生们持续30年努力的结果。
然而,获得名称和进入体系,并不意味着学科的真正成立。盖一事之成、一物之立,不仅需要正名,而且需要责实。
诚然,如果仅就中国书法在本土乃至汉语文化圈的历史传承之丰富、历史遗产之博大而言,说它早已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门类,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学科”的舶来品以及现代学术的性质,决定了其治学路径、方法和规范——借用托马斯·库恩的术语,也就是“范式”——与传统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如何处理这种差异,一定意义上说,至少是近60年来所有从事书法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人所不能不面对的挑战。
传统书学的典型学术范式,自宋以来,以题跋、札记等为大宗,虽然也不乏力求自成体系的著述,但置诸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在德、功、言三不朽价值观中,甚至连立言的资格都未必谈得上。近代以来,引进西式学术概念,草创西式学术论文和著作,书法的学术研究迎来现代转型。但学科地位的不明确,使得转型步伐十分缓慢且充满不确定性,更多时候是依赖于某些个体的自觉与不自觉的努力。不少探索,实不出于书法本身的需求,而来自其他学科的溢出,比如宗白华、邓以蛰等学者的美学研究。
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书协的成立、硕士教育的开展以及《中国书法》《书法》《书法研究》《书法报》等报刊的创办,开始为书法学术研究搭设越来越多常态化的人才培养机构、研究阵地和交流平台。这之后的书法研究,现在看起来,真如跑马圈地,似乎任意一个话题、一篇文章或一本小书,都可能具有“填补空白”、“开辟领域”、“引领潮流”之功。令人诧异的是,学术转型的步伐在这种体制层面上全方位支持的态势下持续加快,于是跑马圈地的许多成果,在不断更新的理念、方法和材料等等的映照下,很快成为明日黄花。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给后来者的,大多数竟然是运用较为传统的史学方法而获得的成果,书法学术评审中出现了史学成果远超美学、理论成果的现象。究其原因,固然有不同学术研究领域自身的特点在,但也不能不承认,与整个书法学术转型的历史积累严重不足有一定关系。
之所以要简单追溯这一过程,是因为摆在我面前的这部由李一先生担任指导教师、王谦先生所著的《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让我看到了一个重要突破已经来临。
我曾在采访中谈到,当下书法发展的重大使命之一是“清理家底”,只有充分了解历史,才能筑实当下、放眼未来。应该承认,这一方面的工作,由于前述传统史学方法较为广泛地被运用,加上信息技术条件的支撑,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与文、史等传统学科相比较还有距离,但是就书法学术研究本身来说,也已经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础。本书的第一个重要优长正在于此:极为扎实的文献功夫。曾经的复旦文科学历,使得作者深谙文史研究的材料体系,具备强大的文献搜集、整理以及解读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解读”能力又是其核心。扎实的文史功夫,不仅使作者避免了字面误读(这仍是近年来不少书法论著常见的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使作者的解读常常能够超越书法本身而深入文化的深处。其精彩处,尤其集中在第二章《书学理论》,其“举隅”“辨微”“文采与机锋”等以及遍布于全书的对文献的解读,在在显示了作者的功力。诚如作者所指出的,沈氏书学思想具有“高密度”特点,因而在解读上也就产生了“高难度”。“高密度”,一方面源于沈氏表达的简约,另一方面源于沈氏学问的博大。解读者未必能够达到如此的博大,但至少在解读时必须深具此眼,否则就可能拘泥字面意思、固步书法一隅,难以真正从“通人之学”的广度上体悟其思想的高度。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已经显示,古代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如水乳之交融,不能由书法而进入文化,就难以深入沈氏这种通人的思想深处。作者的文献解读能力,保证了本书真正具备了追问沈氏思想精粹的可能性。
以此为基础,作者构建了一个十分严密的个案研究的体系。表面上的框架并不复杂,第一章论述沈氏的生平、学问与诗歌,第二三章分别论述书学理论与书法造诣,最后一章讨论沈氏的书史地位与意义。但其内在脉络却极具创造性:以沈氏自身的书学与书法为明线,以历史上的“通人之书”为隐线,从而将沈氏之书这一个案研究,拓展为整个中国书法统绪的重新梳理。作者事实上“重构”了中国书法的历史发展脉络乃至价值体系。在这个层面上,本书超越了基础性的史料挖掘等文献层面的价值,也超越了一般性的分期框架等叙述层面的价值,更超越了常态化的个案研究等具体层面的价值,探及了最为根本性的史观以及中国书法的特质问题。
如前所述,近代以来的中国书法,是对标西方体系中的“艺术”来建构研究体系的,核心概念和命题其实是由西方艺术理论提供的。在这种体系之下,属于中国书法自身的史观,严格讲是模糊的,至少是未经深度反思的。通常而言,我们按照前人曾经给予过的概念、命题来书写中国书法史,比如“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或者试图按照西方艺术的某些概念、命题来书写书法史,比如“汉末书法自觉”、“晚明浪漫主义书风”等,或者通过前二者的结合试图找出“融汇中西”的新路径。应当承认,无论哪一种路径,都使得中国书法研究在近代以来特别是近4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也不可否认,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些模式都已经遇到了瓶颈。近些年来的不少书史研究,除了在文献方面能够贡献若干价值之外,少有能够触及范式层面的成果。如果一定要寻找的话,也许运用了西方艺术社会学方法的若干成果,还能有这样的意义。这些成果,打破了传统的就书法论书法的封闭式研究模式和路径,打通了书法研究与社会史、观念史乃至思想史研究之间的界限,从而提升了书法史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价值。但深入地看,即便这些广泛引进社会学方法的新的书法史学研究模式与路径,也仍然总体上是西方艺术史研究范式的衍生品,而不是真正奠基于中国书法自身的,尤其未能提取出真正出于中国书法自身的核心概念与命题。
书法依托于汉字,因汉字而获得书写者与天地万象的交通契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即“象”而“心”,又因书写工具特殊而得以不断完善内在交融机制,最终演化成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其所呈现于世人面前的,自有文字开始以至明清以来专供悬挂欣赏的作品产生之前,似乎不过技艺而已,在大多数时代,被视为“文章之下”、“六博之上”,甚至有时被看作“学问中七八乘事”,但至少在唐人看来,最晚不迟于汉代后期,“翰墨之道”已经生成,因而在终极的价值追求上,或隐或显地长期以“道”为鹄的。表面看来不过是通音问的信札、备记忆的手稿这类“应用性”的书写,竟然也可能因为充满文化意蕴因而直接成为时代乃至民族文化的表征,如“唐诗晋字汉文章”中的“晋字”。在此机制下,尽管历代对于不同书写的价值评判颇有差异,如南北朝时期贵族鄙视为人驱役的工匠书写、宋代文人自重科举出身的文化特权而贬斥技术官的书写等等,但在历史之河反复流动冲刷之下,所有书写都有可能在“道”的返照之下,重新获得认可,如魏晋南北朝穷乡儿女造像之被清人推崇为经典。
以上诸关系或可粗疏地概括为若干组矛盾统一的关系:肇端于“象”,浚发于“心”;示相于“技”,寓意于“道”;外化于“用”,内化于“文”。前两组,与一般定义下的艺术并无根本区别。而最后一组中的“外化于‘用’”,使书法成为一种普泛于世间的活动,有文字处即可能有书法,似乎并不如常见定义下的“艺术”那么高级,那么超越功利地专门用来追求精神享受。与此同时,“内化于‘文’”,则又使书法在读书人中长期处于特别的位置,在与日常生活始终密切联系的同时,直接透入文化中最为精粹的部分。这一组矛盾,使书法具有一种常见定义下的艺术所不具备的特质——向文字所及的整个世界无限敞开,接受整个历史文化的滋养,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无限定。
这一特质,造成了许多困惑。其中最为重要的困惑之一就是近代以来产生而现在已经解决了的“书法是不是艺术”的身份困惑。第二个最为重要的困惑,则是“什么人才是书法家”的身份困惑,也可以表达为“具有什么样的素养才是书法家”。
“通人书法”,可以从理论上解答这两个重要困惑。
中国书法具有艺术的全部性质,却并不仅仅为审美而存在。向下可以通乎最为世俗的生活,向上可以揭破天道人心的奥秘,居中还可以辅翼教化人伦。就其下者而观之,在世俗的日常,它不过是一种技艺;即使上升到教化人伦的层面,也不过是一种工具性的手段;然而一旦进入天道人心的追问,那简单的一笔一画,却都可能本乎天地之心、取会风骚之意。更重要的是,这上中下的层级,并不是分离的,而是浑融无间地通过笔墨寄寓于永不停歇又无时不在的书写活动之中。漫长的历史,将书法熔炼在几乎整个生活和文化之中,无法剥离。书法由此“通”于万物,“通”于生活,“通”于文化,乃至“通”于大道。
相应的,书法家也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存在。穷乡儿女造像、官府文书、日常人家尺牍、文士手稿等等的书写者,都可能经由书法经典的训练和无所不在的书写活动而触摸到深藏于笔墨之中的妙道,从而成为不同层次的书法家,创造具有不同价值的书法作品。“通人”,就是这种种不同层次书法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所谓“通人”,王充指为“博览古今”。古、今,并不局限于时间的积淀,无论是古还是今,自身均是包罗万象的。书法家而称“通人”,必是勘破了“心”“象”、“技”“道”乃至“世”“文”之间的种种界限,真正做到囊括万殊裁成一象者。
历代书论中,“通”既可以在技巧的层面展开,如欧阳修的“因见邕书,追求锺、王以来字法,皆可以通……凡学书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馀”;也可以在字体层面展开,如孙过庭的“旁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还可以在意的层面上展开,如苏轼的“苟能通其意,尝谓不学可”;更重要的,是在心物墨(心即人,物即天,墨即书,三者合成,就是天人与书法)层面上展开,如张怀瓘的“心不能妙探于物,墨不能曲尽于心,虑以图之,势以生之,气以和之,神以肃之,合而裁成,随变所适,法本无体,贵乎会通”,又如孙过庭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回看历史,不难发现,在这个概念的映照下,当代一批前辈大家,如前举浙江美院的陆老、沙老以及林散之先生、启功先生等等,事实上践行的正是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通人书法”之路。甚至可以说,当赵壹《非草书》中指出张芝书法活动的特点是“博学馀暇,游手于斯”之后,这个传统便已经存在,并且演变为几乎历代所有最具代表性的书家的共同特色,凡是能够站到中国书法巅峰之上的书家,少有不可以称为“通人”的。
基于上述,窃以为,王谦先生通过沈曾植个案研究所提出的“通人书法”概念以及所指出的“‘通人书法’作为书法传统之一脉确实存在,且形成潜在传统”的判断,在中国书法研究范式的转型特别是概念的淬炼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通人书法”完全有可能作为核心概念之一,进一步揭示书法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活动的特质,也完全有可能作为核心概念之一,进一步深化中国书法史的研究乃至重构中国书法史的写作框架,从而构建起一种真正立足于中国本土的书法研究范式。以此为出发点,王谦先生或能拓而广之,为中国书法研究开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若干年前,本师欧阳中石先生即已指出,书法不仅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文化。进而还指出,书法家的文化素养,其实不是“字外功”而是“字内功”。书法与其所生存的日常、所依托的文化之间,完完全全是打成一片,无可拆解的。对书法艺术的研究,不应止于“艺术”范畴,而必须扩大到“文化”;对书法家的要求,不能止于笔墨,而必须扩大到学问,延伸至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前述的“特设”,倒反而为我们创获像王谦先生这样真正揭破中国意蕴的书法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我追随先生日久,奈何学养不足,一直未能在研究上实现先生的愿望,今见王谦先生论文,凛然而觉得欧阳先生当年的设想,终于在研究论著上有了杰出的回应,既自感惭愧又为之欣忭。复蒙作者以序相责,略志杂感如上,即以乞正于王谦先生以及阅读本书的大雅方家。(叶培贵 2020年8月8日)

作者简介

王谦,艺术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曲阜人。198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2019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研究著述20余部。《从“通人之学”到“通人之书”:沈曾植书法研究》《沈曾植碑帖题跋札记辑释译论》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古代书论八大家辑释译论”(8卷)即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