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卫平从来没有抗拒图式的传统,他的成长之路上受到过规范的程式甚至动作的磨炼,其写意花鸟画无论题材还是语言,显而易见地见出与传统的链接,只是“链接”中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他的私人状态,包含了他的人生过往、修为气质、脾气秉性的所有信息,其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当然,风格的形成并非仅仅是有赖于“笔墨”。或许源于王卫平少年曾有过学习工艺装饰的经历,他对画面整体的形式构成、节律有着敏感而独到的体验。对画面形式的营造激活了程式的传统,解构了现实的物象,重新架构了他心中的时代气象。长期以来,我们囿于“国画现实主义改造”的思维闭环中,将本已“得意忘形”的文化诉求重新降维于“见山只是山”的写实刻画,尤其是美术院校单一的教育体系炮制了单向的创作模式,谱成了当代美术创作的写意殇歌。王卫平求学的年代,正值冲破现实主义桎梏的时代新潮,“形式即美”的艺术观念正应扣年青者心灵的不羁与律动,他们似乎更钟情于诗性的具有节奏的语言。点、线、面可以是无穷尽的节奏变化,他用这些节奏重新“经营位置”,从而把传统的意象编排出新的旋律,或动,或静,或瞬间即逝,或跌宕起伏。中国画本就有“画是无声诗”的原理,诗之所以是诗,当然是表现主义的,它的本体当然是具有形式的语言,若非如此哪来的什么韵律,至于韵律之外的余味更无从谈起。王卫平写道:“纵观历代成功的画家,作品无一不是在形式感上有别于他人,有独到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形式感强的作品更容易映入眼帘,更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好奇,并给人以启迪,也更能激发观者选择观赏的欲望。”我服膺于王卫平的此种见地,暗暗思忖这不就是禅家所说的“见山不是山”的那层境地。画画只是画画,从来就不止于画东西,如果花鸟画只是栩栩如生地描绘“鸟语花香”,那太乏味,没有“我”的风景还有什么意思?王卫平没有固守写意花鸟画旧有的窠臼,作为接受过现代美术教育的当代画家,他的视野与知识结构是宽阔的,他放开心胸去想象,营造心中交响乐般的场景,在他的大景创作中,我似乎听到贝翁题为《田园》的乐章。遨游在乐章的回荡里,直欲“乘兴两三瓯”,“但教有酒身无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选甚春秋。”
王卫平有一帧小品题为《飞过一道道坎》,一只无名的鸟掠过有月的夜,画的下方放笔直取飞白,率性地写出几笔不知名的草,轮月的周边是淡墨清透的天色。与那只鸟的白眼对视,当时惘然。艺术的苍穹之下是现实的生活,寂寞的诗心来自宇宙之无穷,或可垫平无法逾越的生命沟坎。古人曾说画是可以“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的。王卫平从来没有忘却生活的恩惠,一路走来,从胶州到京城,从京城到蓟津,沟沟坎坎中奋力举翼。他不遗余力地在生活中感受,穷尽手段收集自然的素材。真切的写生体验使他并没有落入形式主义的空洞陷阱。王卫平的写生既不同于宋人“格物以致知”的谨严审物,又不同于近现代舶来西学的“定点作画”,他并不沾染花鸟画“写生正派”柔媚萎靡的习气。他身似不系之舟,托体造化之间,走马观花,优游摄情,在自然的温怀里活脱得像个顽童。每次玩赏他写生归来的收获,但见花如欲语,禽如欲飞,石必崚嶒,树必挺拔,其中颇费剪裁。我常想他大概只是在旅途中看到了他欲画的物景,而不是记录了他看到的景物。生活林林总总,世相郁郁蓊蓊,这世上的观法源于观念,你哪能什么都看得清。有人说诗是糊涂人写的糊涂话,那么画是否是糊涂人描的景。王卫平还有张画叫《繁英落尽果实红》,飞花寥落后空寂地泼墨,在雨中吗?或是在晨雾里?抑或在暮霭间?一场虚虚恍恍、黑黑白白、红红赭赭的空境,假如时光在此停滞,我愿呆得什么都不想。
当飞过一道道坎儿,我们学会“允许”,淡淡地安于“日月掷人去”,不再去慨叹“逝者如斯夫”。去岁的秋季,王卫平辞去了画院的副院长职务,出版了一本画集,举办了一场画展,在朋友的真挚祝贺中告别职业的生涯。我当然不舍这同事、同乡的情缘,然而进而又想艺术又何尝是一种职业,因此祝贺他的自由。陶渊明曾感慨:“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或许正是人生与艺术的起点。王卫平终于下维扬,渡巴峡,上黄山,走青海,寒来暑往未及秋,已是画囊盈满。
我艳羡于他的壮游,有时却想:待大兄归时,不如约场酒吧,也温一壶月色,细说我:“随风去住,随波舒卷,人也如鸥倦。”
王卫平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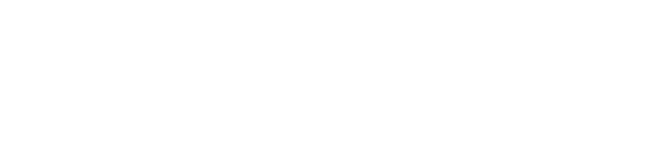



(文/孙飞,来源:中国书画报)
画家简介

王卫平,1963年出生,天津画院原副院长、艺委会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理事,文旅部艺术基金专家评委。
近年来作品二十多次入选由中国文联、文旅部、中国美协等单位主办的全国展览,并九次获奖。曾赴新加坡、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区举办画展,五次出版个人专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