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天衡四岁写字、六岁刻印,在方寸之间徜徉近八十年。他对篆刻艺术的感知、他在作品之外的心声,日前具化为一场展览,呈现给观众。历时五个多月的《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2021年5月5日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落下帷幕。展上包含国家一级藏品逾百件,其中,西泠印社借来的50件(套)一级品,有些甚至是第一次出库房。展览更向海内外藏家商借珍品,集结十分不易。这位事必躬亲的策展人在开展后即大病一场,愈后却说:“我实际上还不算满意,本来我还有一些想法和构思。三个月医院住下来,这个展览要接近尾声了,我不能让它就这么结束。所以我一个个联系印学专家,请七位来馆作专题讲座。再加上4月24日做两场沉浸式互动,把这一块就补上了。我们还要出三本书……”
“不惜力”的韩天衡,在印学方面也著述颇丰。20世纪80年代初,他受西泠印社编辑部之托编订《历代印学论文选》,之后又编制《中国印学年表》《中国篆刻大辞典》《中国印学精读与析要》等。“访书、读书、抄书、收书”六十年,韩天衡近期还将推出《中国印学年表》第四版:“最近十年读了几亿字的史料,整理出不少于4000条条目,真是海底捞针、深山探宝,读一本书里面可能只有一两个条目是可用的,但总让我感到充实和兴奋。”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苏州。2015年以最高票获中国书法兰亭奖艺术奖,2019年获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近日,记者记者探访了这位元气复又淋漓的篆刻艺术家和研究者,请他谈谈印章的学术与源流,也展望篆刻艺术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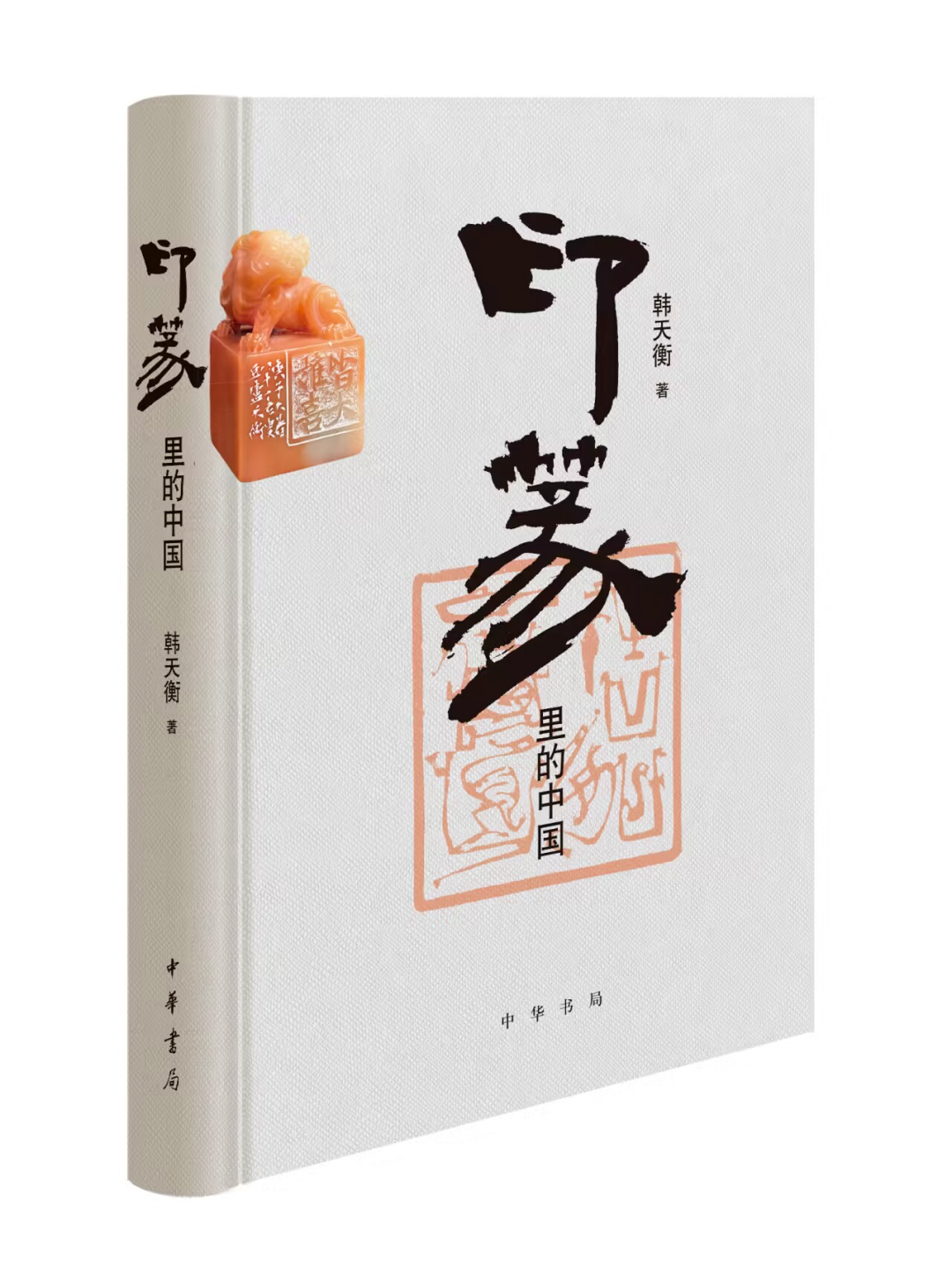
篆刻不是小众艺术
记者:您曾经说,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的习艺生涯都是由篆刻起家,继攻六法,进而会通书画的。然而篆刻似乎一直挺“小众”的。能说说您是如何想到做这样一个大展的吗?
韩天衡:对于印章,今天的人们是既了解又不了解。现在称篆刻为小众艺术,实际上这个定义不太准确。印章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不是偶然的。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始于实用。当原始社会演变为阶级社会,有了政务、军事、商贸、人跟人之间的交往,就必须有辨伪鉴正的物事——口说无凭,你说你是将军,让我怎么相信你呢?做一笔交易,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诈骗呢?今天科技发达了,有身份证、人脸识别,那时的证明就是先民以智慧发明的印章。
直到五十年前,领工资、领包裹都还要盖章。虽然今天这方面的使用少了,但政府机构、任何一个企业,还是要有一个公章。而且印刷得还不行,一定要用印泥钤盖。所以,印章从商周到现在,三千年绵延不断地在使用,至今仍是整个社会公认的、普遍通用的证鉴。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凭信载体,它的使用既广且久,人们一定会在上面加以艺术性的表现。说它是小众艺术似乎是“小”了点。
印章到今天,已经从实用接近于走向纯艺术。我对这门古老而有内涵的艺术,是情有独钟的。但就我个人的接触,没有见到有一个博物馆、美术馆做过相对全面的印文化展览,我构思了两年,就有了《心心相印——中国印文化大展》。为什么前面要加中国两个字?因为就整个世界文明史来讲,最早的印章出现在中亚地区。他们的印章上偶尔有文字,但更多表现的是图案;材质上,使用的多是玛瑙。后来他们的印章传统戛然而止了。
记者:此次展览汇聚了西泠印社、河南印社、韩天衡美术馆和海内外诸多鉴藏家的珍品,其中有不少孤品印谱。这些展品对于展览的完整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吗?
韩天衡:我的构思是做一个全景式的、有深度的、代表性的呈现。那么,放什么,不放什么,为什么要放,可能单单看展品是说不出来的。因此这个展览也从单纯的实物展示,变成了一个结合学术的活动——在展品边有一些介绍评述,举办讲座、雅集等等。
展品上我们安排了五个单元:周秦两汉的古玺印,明清以来的文人流派印,印谱,印石和印纽。实际上如果将印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包括进去,何止这五类呢!盖印谱的纸、打图章的印泥、钤拓技术、刻刀……但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几项内容也很丰富了。所以人家来看展览不会感到寂寞——做学问的印学家,特别重视印谱;篆刻家重视印面,文彭怎么刻,何雪渔怎么刻,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难得一见的。
就说说学问家看重的印谱文献吧。从北宋开始,有了印谱的汇辑。最早的一本是杨克一《集古印格》,比《宣和印谱》还早。我们展出了142部珍贵的历代印谱,其中包含明代最重要的三本印谱:《顾氏集古印谱》《范氏集古印谱》《松谈阁印史》,这些印谱为明清文人流派印的勃兴提供了最重要的艺术上的经典模范。著名的所谓“三堂印谱”,明代的《学山堂印谱》,康熙时的《赖古堂印谱》,乾隆时的《飞鸿堂印谱》,我们都有展示;还有历史上一直争论不见头绪的《孝慈堂印谱》。
展会里面特别珍贵的东西甚多。有一本《黄秋盦印谱》是嘉庆初年的。这本印谱的可贵就在于印章附有了边款。想想碑帖有多少宋拓本啊!一人多高的碑能拓下来,一方那么小的印章边款拓不下来吗?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做不到,而是没有想到。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不知道这部印谱的特殊意义。

篆刻艺术的第二个高峰还未到顶峰
记者:篆刻艺术在古玺秦汉印时期就十分辉煌,然后照您的说法是“相对式微”了上千年,到明清又出现一个高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面貌?
韩天衡:可以说,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里,篆刻是成熟得最早的传统艺术之一。诗讲唐诗,词讲宋词,书法称魏晋。但实际上在印章艺术成熟的战国时候,很多艺术还在萌芽期呢。而篆刻艺术能有两个高峰,也是其他艺术门类所没有的。因为它具有其他领域所不具有的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因素。我认为有这么几条——
一是材质上的革命。古玺印的材质是青铜,偶尔有象牙、木、竹、玉,到魏晋以后,篆刻艺术渐渐式微。但宋时,文人开始爱好追逐金石,他们喜欢印章,也想要进入这个领域。可是,文人尽管熟悉、会写古代文字,会构思印章,却没有镌刻铜印的腕力,所以在漫长的宋元时期,包括米芾、赵孟頫,他们的有些用印都是写好以后找工匠去刻。但合作毕竟不过瘾,最好自己一手包办。明代后期,新的石材如青田石、寿山石被广泛引进到篆刻领域来,文人这才找到了理想的印材,再不用假手于人,可以自己篆自己刻,其乐无穷。
二是有了原打印谱。过去的印谱都是给工匠随性的刻板墨印,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能显示出古玺印的本来面目。明代隆庆时期,1562年,松江顾从德第一个想到用他收藏的周秦两汉印直接原印钤盖成印谱。这部《顾氏集古印谱》里有1700多方印。后来的《范氏集古印谱》有3000多方,《松谈阁印史》也有1000多方。画画有写生,而书法篆刻没法写生,入门只有临摹一途。这6000多方古代经典的原貌呈现,给文人的篆刻创作提供了最好的经典范本,让他们有优秀传统可以借鉴。
三是创作主体队伍的变化。文人成为印章的制作者。文人通古文字、有学问、善思量,有很好的变通能力。至少这三大要素促使了明清文人流派印成为篆刻艺术史上的第二座高峰。不过,从三千年的历史来看,周秦汉魏之外,明代后期到现在也只有五百年,而且还在蓬勃向上,所以我认为我们第二个高峰还没有到顶峰。诚然,第一高峰是以诸侯国和时代、地域为艺术特征,而明清高峰则是多以个人艺术风貌为特征。当然边款艺术则是其中又一新创造。
记者:我们现在讲“书画印”,印章似乎成了书画的附属品。能否请您谈谈印学的学术地位?
韩天衡:过去篆刻往往是附属于书法的,现在基本上能够独立出来,已经说明了这门艺术越来越兴旺和发展,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可。
明清以来的篆刻家大都是业余的,开刻字店的往往不是篆刻家。但其实社会的观念一直在变化。明代后期,按苏宣的说法是“家家仓籀,人人斯邕”。像文人李流芳、王志坚、归昌世三个好友就经常在一起刻印,标榜秦汉。王志坚后来考取进士做官了,就不刻了,彼时好事者要把他的作品收到书里去,则被他删去姓名。当时毕竟觉得这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毋需署名。然而明代后期也开始出现第一批有文化的职业篆刻家,如何雪渔、苏宣、朱简等等。
我们过去笼统地将篆刻也归纳为金石学,这是大而化之的。印学是金石学一个分支,但自有精深广博之处。印章与印谱的史料价值殊为可观。我们从印章、封泥、印章边款以及印谱序跋的文字里,可以了解到印人的性情与交游,以及正史不载的丰富史实,补足遗缺,充实考订,意义匪浅。曾经,上博研究员孙慰祖就通过一小块残碎的封泥,准确地说是留存的几根篆书线条,考证出长沙马王堆三号的墓主人是利豨。
不过我的私见,有清一代对印学理论的研究还不及明代晚期的几十年。乾嘉以后小学和文字学研究的深入是新成果,已不单单是印学的问题。但就印学理论本身来讲,还要推明末。印学论著多达二十余部,像周公瑾《印说》、朱简《印品》、徐上达《印法参同》等等,讨论篆法、章法、刀法、意趣乃至创作态度,由形而上抵形而下,在印学理论方面有一个颇见完整的体系。
真正异军突起的是最近这四十年。可以说,篆刻艺术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取得成就最大的艺术门类之一,且对整个印学史的研究,对个案,都有深入地挖掘、收集、整理与考证。诸如,四十年所出的印谱数量要超过宋代到民国的总和。这种印学研究的深度、广度与多元性都是历史上不可比拟的。这是前所未有的繁荣。
“印宗两汉”,然而汉印也不单单就一个面孔
记者:今天的许多篆刻作品据说都好走极端,或是极度精工,或是极度写意,相比之下,平方匀整有隶意的汉印风格倒是少见了。您觉得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况?
韩天衡: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这么看。好的汉印始终是篆刻的基础。“印宗两汉”是明代后期的提法,这在当时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那时候的篆刻脱离了传统的、有高度的审美轨迹,充斥印坛的多是宋元屈曲盘绕的九叠文官印,和气格低劣的粗陋私印。是汉印滋养了明末第一批好印的文人。不过,为什么不号称“周秦两汉”呢?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认识放在面前的周玺秦印。像明代朱简、康熙时的程邃,他们也摹拟古玺,而且《顾氏集古印谱》里就有,但他们当时由于知识的局限,不知道这是战国的东西。
实际上,在明代有实践的印人已经注意到,一味宗经典,会变得“有古而无我”。你不能为其束缚,否则有汉要你干什么?艺术史始终是少数杰出人才的创新史,而理念的创新决定了你的作品有否创新,所以我想今天出现许多不走汉印“正统”道路的印人,也自有其原因。
我们要知道,从明代后期文人篆刻兴起一直到现在,汉印始终没有人会抛弃,但真正搞创新的篆刻家都知道这是牛肉羊肉,是好东西,一定要吃,但吃了以后不能身上长牛羊肉,而是要化成自己的精气神。
记者:篆刻艺术在历史上有哪几次大的创新?
韩天衡:就从丁敬身说起吧。他是乾隆时的人,很睿智,他写过这么一首诗:“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如岭上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他说汉印是好的,但也不要单一地只吸收汉印的营养,实际上六朝、唐宋的印章里也有好东西,应该借鉴。这就是一个新的理念,正因为他有这样一个新的理念,他自己的实践就突破了周秦两汉。他拿周秦两汉一直到宋元明凡是好的东西都借鉴发挥,把“印内求印”这条路都走过了,营养吃个遍。丁敬身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继而开创了浙派。
丁敬身之后,又出了一个邓石如。邓石如另辟蹊径,从印章里走出来,将书法的妙处引进印章。这就叫“书从印入,印从书出”,于是产生了皖派。所以说,汉印要学,经典都要学,但是复古守旧断不能创新。
现在有些人在学术理论上的见解是滞后的,还老是拿邓石如“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当作一个永恒的理念。可如果这样的话,邓石如后面就不会有一个了不起的赵之谦。赵之谦的视野更开阔,他身处晚清那个时代,五口通商,修建工厂、铁路,出土的文物就更多了——权量诏版、砖瓦碑刻、帛布镜铭。他不单单是从书里面去讨好处,他见到了很多前代篆刻家没有见到的新东西,濯古来新,说他是“书从印入”就以偏概全了,应归纳为“包罗万象入印来”。
之后又出了吴昌硕。吴昌硕也佩服赵之谦、邓石如、吴让之,但是佩服不等于照搬。这里要说到罗振玉,他有学问,但也很守旧,认为汉印里面只有铸印可以学。因为它是失蜡浇制的,非常规范,除此之外的都不能学,尤其那种烂铜印。而吴昌硕恰恰是在“烂”字上做文章。因为失蜡浇制的印始终像新的一样,字口清晰无比;而铜印入土一两千年,受到腐蚀。漫漶不清的印面,是“烂”,吴昌硕则意识到这是人工之外,大自然对这方印章所做的第二次创造。人家刻印都是用刀刻完就算的,吴昌硕刻完以后还要花很大的工夫修印面,敲打摩擦,“既雕既琢,复归于朴”。他知道什么是自然天成,于是产生了那种粗服乱头,但气格宏大的风格。所以说,不断更新的理念,才能产生不断创新的印风。
这些人都是认真借鉴过汉印的,而且千万要知道,汉印不单单就一个面孔。汉印里有铸印、凿印、琢印,风格有规整的,有奔放的,有瑰丽的,有霸悍的。所以还是不能一概而论。不过实际上,古代印章里形式最丰富、章法最奇崛、表现最多样的,是古玺印。这跟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追求个性的强烈氛围有关。而到汉印的时候,已经强调平方正直。在我看来,我们今天以古玺入创作相对比较少。这也是“印宗两汉”的固有局限性。
记者:您曾经讲到,海上印坛百年,“不只是时空的定义,也不是一个流派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更广泛内涵的印学文化系统”。请您谈谈上海同篆刻的渊源吧?
韩天衡:说上海是篆刻之城,一点不为过。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篆刻产生第二个高峰的原因里,有一个就是有了原钤印谱。而原钤印谱就是我们上海人顾从德首创的,是他创出了这个思路,给文人提供了学习优秀传统的最好范本。
而且,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文人印谱,也是上海人首先制作出版的。朱鹤(松邻),也是嘉定竹刻的创始人,生卒年不详,有一本《松邻印谱》,当成书于1550年左右。自明末至民国,上海一直是篆刻史上的重镇,记得二十多年前,有人给20世纪篆刻家搞过一次民间评选,结果十大篆刻家里上海印人占了七个:吴昌硕、赵叔孺、王福庵、方介堪、陈巨来、来楚生、钱瘦铁。当年,还有许多杰出的篆刻家云集上海,而这批老一辈篆刻家在上海又培养了新一代的篆刻家,让上海的篆刻群体薪火相传,有雄厚的实力,也让上海的印学研究、创作、传播与教育体系走在前列。
(来源:文汇报)
艺术家简介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别署百乐斋、味闲草堂、三百芙蓉斋。擅书法、国画、篆刻、美术理论及书画印鉴赏。
现任西泠印社名誉社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上海中国画院艺术顾问(原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上海市文联荣誉委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首席顾问、上海韩天衡文化艺术基金会理事长、韩天衡艺术教育基地校长、上海吴昌硕艺术研究会会长、吴昌硕纪念馆馆长、中国石雕博物馆馆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温州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