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我做了个梦,直到早晨仍不愿醒来。醒与不醒又是一番搏斗,当我意识到要醒来时,试图努力闭上眼睛回到梦中之境,已无可能。我梦到了30年前的人和事,半透明的树林,逆光下奔跑的白色衬衣,无数的蓝色蝴蝶涌上山坡,翅膀一扇一扇地停留在崖壁之上,像铜镜般反射着洒向高坡的阳光,和1992年冬天的霜一起,凝结在少年那还从未刮过的绒毛胡子上。
我还梦到了17岁那年写下的几句话:
那少年
独爱朝阳
忘记了
山坡上
放牧的羊
气死的獾
1997年夏天,年轻的我骑着擦得锃亮的旧自行车,和树上的知了一起开心地扯着嗓子嘶鸣——知了在庆祝终于找到了配偶,我在欢呼终于离开了大学。
自行车是我在二手市场买的,60块钱,终日跟着我欢快地跑来跑去。没有地方画画,就伏在很小的桌子上画很小的画儿。桌子越堆越满,地儿越来越小,最后就画邮票这么大的小画儿,也很开心。只要没人管,我就很开心,就这样过了几年既不挣钱,也不花钱的日子。也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意识到,很多东西总量可能是不变的,这世界不会因为你富贵而爱会多一分,也不会因为你贫贱而笑会少一分,世界自有规律。我想要找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去做,可是最喜欢的是什么呢,也不是很清楚。在没有作品,没有事业,没有一切的时候,反而觉得人生有无数条美丽的道路在等着自己。
离开大学又回到大学,开始了我七年的教员生涯。其中一项工作是每年暑假带建筑系的学生们去写生。开始几年是去安徽歙县、江苏苏州、浙江同里,都是如画的水乡,黑瓦白墙、软软绵绵、吴侬软语、柔柔美美,美是美,终究不是我的调性。后来习书法,我也能感觉到,虽然非常希望自己去喜欢王羲之,可是最终也并没有那么喜欢王羲之,还是更爱魏碑的拙朴之美,硬而直。上了太行山,我才觉得找对了地方,那种雄壮的气息,看不透的苍茫。
太行山之行的点点滴滴在不同时期反复回荡,这是改变我观念的一个地方。所住的郭亮村位于山西与河南交界的林县,路很难走,话也很难懂。一入山中,便看到红色砂岩层层叠叠,崖壁垂直落下,厚重之美扑面而来。同时扑面而来的还有村中的鸡打成一片,面红耳赤,晚上睡在树上;村中的人定时用水,节俭物料,垦山为田,成为约定俗成的民风。我和学生们住在太行山老侯家。老侯的眼睛非常明亮,话不多,牙很白,每天早上额外给我们每人煮一个鸡蛋。去太行山之前都说林县人特别能吃苦,这句话我开始不明白什么意思,人还不是一样的?哪有生来能吃苦的人呢。住了一段就明白了,没有水,没有土地,没有路,只有吃苦才能吃饭。
住下没几天,老侯就紧张地找到我,说他要出去几天,隔壁村住的南阳几个同学进山没回来,几个村的人都发动去找了,他也要去。老侯说:下面几天照顾不好你们,多担待啊。我说你快去吧,心头一紧。两天后,老侯回来了,每天都要反复告诫大家:同学们别自己进山啊,这山一进去就迷路了。我忍不住问,找得怎么样了。老侯低声叹道,找到了,人没了,两个人。又专门嘱咐我,特别是稍微熟悉了山路之后,更要小心,你觉得好像知道了怎么上下山,真的进了山,看哪儿都是一样的,就转向了,非常容易迷路。上山容易,下山难啊。
老侯教我学会不少东西。
观看悬崖是跟老侯学的。他每日带我去看山,行走一条山路,攀爬一段险道,见识一番美景。前后无人,我便大声歌唱,老侯远远看着我发笑。登上山顶,离悬崖10米的距离我们停下,他让我趴在地上匍匐前进,最后只把头露出来。老侯说这样比较安全,可以看到悬崖之下。我果真看到了崖壁山谷之下眩晕般的壮丽。老侯说这里山风很大,如果直接走过去,一阵大风刮来可麻烦了,不能大意。开始上山的时候,我总是走得很快,老侯在我后面边追边喊:“你慢点儿,你慢点儿。”又教我,“山路需要一段一段熟悉,别着急,一天走一段,上山一条路,下山一条路,到岔路节点多记下石头和树,多来几遍,脑子里慢慢就有地图了。”
太行山险峻,上下山都不便。上世纪70年代,村民自发开始在崖壁上凿刻出隧道,决心在石头里开一条下山的路。崖壁上的“隧道”在漫长的手工劳动中诞生,现在已经可以通车了。我问老侯,之前呢,之前你们下山上山怎么办?老侯说我带你去看看?你想走近道还是远道,远道好走,就是远,要转好几个山。我说近道呢。老侯笑了,近道怕你下不去。我说,试试。第二天我们先走了一段下山的坡路,然后走向悬崖尽头的一个缓坡。老侯指着悬崖下说,这是条近路,在石头缝里钉上绳子,拽着绳子慢慢顺下去,以前很多东西都是从这里背上来的。我看了看绳子和直落的崖壁,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手艺下山。我说,我们还是走远道吧。这就是太行山的艰辛,交通不便、水源短缺、种植困难。
捉蛇是跟老侯学的,没有诀窍。老侯平淡的说,山里的事其实没有诀窍,方法对,多练几遍就行。然后睁大眼睛看着我:“在山里最重要的是不要怕,碰到什么都不要怕。在山里怕也没用,没人能救你,你得自己掂量,有没有危险,有多大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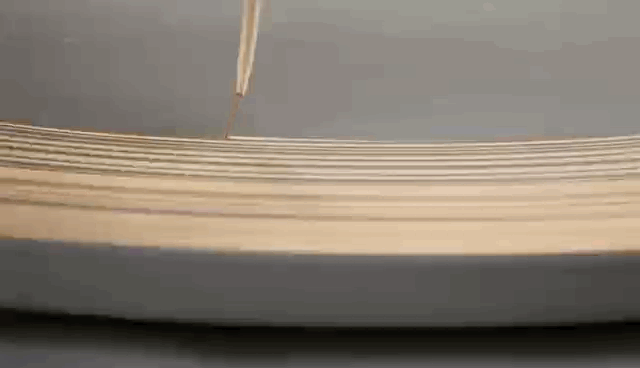
创作过程
一日,我们在山上看到了一张褐色黄点儿的蛇衣挂在灌木上,漂亮极了。我正准备上前近看,“你别动。”老侯一把拉住我,然后拿棍子在周边的草丛里打了打,向我解释:“这个蛇衣太新鲜了,可能刚蜕完皮,也许还在附近,你看不到它的。”然后用棍子挑起蛇蜕,很长的一条,递给我说:“上山手里一直要拿根棍子,棍子的用途很多,关键的时候是救命的。有高草和灌木的地方,你就用棍子打一打,如果有什么小动物啊,蛇啊,它们会逃走的。”他说捉蛇也是如此,首先是不要怕,然后看是不是毒蛇,如果是毒蛇千万别碰。真被毒蛇咬了,下山来不及,山下的人赶上来也来不及。毒蛇头是三角形的,脖子猛一细,尾巴也是猛一细。无毒蛇也要谨慎,如果不捉,尽量别碰它,是蛇都有危险,绕道走就好了。如果下了决心要捉——一定要快,要果断,以快取胜。“这山沟沟有很多蛇,蝮蛇最厉害,山里还有野猪、野山羊、狍子、狗熊、豹子,人活动的地方都看不见它们。”老侯说,“二十年前我们村里人还一起捉过狗熊,现在不让了,其实还有,那些豹子和狗熊在哪里,我们都很清楚。”我说,你就吹吧。老侯凑近问我,你要不要豹子。我说算了算了。
现在想起来有些话很像哲学表述,当年说得时候都是当家常聊的。后来两千零几年的时候,在吕品昌老师工作室浮雕板后面也发现一条蛇,有孩子在,吕老师迅速地捏住了它的头。我一看这个身手就知道他小时候肯定学过,吕先生说江西山里这种东西很多。生活即哲学。
每年相处几十天,我能感受到老侯的热心和温暖,务实、善于琢磨,乐于助人。我觉得他应该是个很聪明的人,可我也能感觉到,老侯在村里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中国乡村就是小社会,都有村中能人,有懒汉,有热心人,有霸王,有无赖,有村落的阶层分布。在我看来他过于谦卑,对村里的几乎所有人都点头哈腰。我问老侯,村里人都是沾亲带故的,你怎么这么客气呢。老侯笑而不语。
也是在太行山,我第一次体会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那天中午时分便沙尘漫天,天色猛然暗下,乌云滚滚,大风灌进房间,整个房子好像都要飞起来,然后是瓢泼大雨,没有尽头地下着。我们躲在老侯家用石块垒起来的房子里闲聊,听着呼啸的风声。不知怎么说到人生如何美妙的话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轮到我了,我说,人生美妙,无非妻女如花、大同天下。学生们觉得好像这话很厉害,问什么意思呢。我说“妻女如花”不是说你的夫人和女儿都很漂亮的意思,而是说你女儿到了如花般十六岁的时候,妻子可能已经四十多岁了,如果您那时仍然感觉妻子如花,那是真得爱她。小家搞好了,天下大同就不远了吧。又有一个同学问我,老师,你说人活着干嘛呀。我心想这话才是厉害,我怎么会知道。但我是老师,嘴上不能这么说。想了想,我说人生两件事: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有同学喊,我喜欢做的事就是爱喜欢的人。我说,厉害,雀巢咖啡——二合一。大家哄笑,伴随着大风灌进石屋的鼓鼓声。

2021年,郅敏在景德镇创作。
这些闲聊的话说过就过了,早忘记了。两年前问我问题的老学生来北京相聚,又笑谈起太行山往事。我说,当年你20岁,我也才24岁啊,现在看都是孩子。你不知道人活着干嘛,我怎么会知道。他说:“老师你说得没错,只是很难做到。我记得这些话是因为当年觉得你有少年之心。”我说我现在还有。
2003年,我最后一次上太行山。临别前几天,我和老侯一人拿了根木棒再次上山。坐在山坡上,看着几年不变的大山,我对老侯说我要回北京上学了,明年不能保证再来了。老侯说你不来我去看你,说北京好啊,你好好干啊,带我去看看天安门,别说北京,省城我还没去过哩。
回城的前两天,老侯招呼我,你来看个东西,把我带到后院。我看到木桌上放着个铁笼,一个黑白相间毛烘烘的东西在铁笼中躁动。我问这是什么,老侯说是獾。我问这是哪来的,老侯说你不用管是哪来的,你们过两天回城,就当我送你们的心意,把我推了出去。当夜和学生们看画、闲扯,我说后天回程,老侯准备了只獾。学生们说,估计味道不错。
当夜没有睡好,我准备了一番话让老侯把獾放掉。第二天早上敲开房门,老侯不在,小侯说爹一早就上山了。我问儿子那只獾哪儿来的,儿子说是他爹60块钱从隔壁村农户那里买来的。上午,老侯回来,我说我给你60块钱,你把那只獾放了吧。
老侯说,獾已经死了,气死了。
老侯带我去看那只獾,还在笼子里,已经不动了。我摸着它脚心厚实的几个黑色肉垫儿,还有一丝温度,磨砂的皮肤,很有韧。那种手感让我终生难忘。我的手摸着它的脚垫,爪子上全是褐色的血渍,可以想象最后一夜的痛苦。老侯抱怨,“獾的气性是大,但这只獾的气性也太大了,我还放了玉米在笼子里。”告诉我獾很聪明,皮厚,毛厚,晚上出来,什么都吃,气性也大。我问什么叫气性大。他说和有的人一样,很傲气,不能关着它。我明白了,野生的动物,骄傲的动物。
我说,老侯,我还是给你60块钱,我们把它埋了吧。老侯明亮的眼睛看了看我,非常迟疑地说:“好吧,这东西现在不容易搞到,本来你要真不吃,我就准备放冰柜里了。”吃完午饭,我俩拎着獾在山边小槐树边上埋了。埋完之后,我说我后天走,我们再去转转吧。“周边都去过了,我带你去看日出吧。”老侯仰头看了看天说,“看样子明天的天气应该是可以看到,你早点睡,夜里两点出发。”我说这么早啊。他说不早,晚上走得慢。当夜穿上厚衣服,在漆黑的夜里拽着老侯的棍子出发,打着手电步行两小时到达了目的地。这是较高的一座峰,从来没有来过,四周都是黑的,只有天是深蓝色,满天星斗。老侯指着崖对面的几座峰说:“你看我们走这么长的山路来这里,是因为这里有三座山崖聚在一起。这里的日出最好看。我们坐在这里的是一座偏北的峰,东边还有一座,不是很高,一会儿太阳会从那个地方升起来。”又指着西南方说,“我们的西南方还有一座峰,更高,所以第一缕朝阳会洒在这座崖壁上。”

郅敏:“2021年在景德镇创作,在烧制完钢筋和火山岩之后,一只蝴蝶落了上去。”
在丝绒般的深蓝色天空下,我们抽着烟,听老侯讲村子里的故事,谁和谁相好啊,谁和谁有仇气……说他不是这个村的,是外乡人,倒插门的女婿,年轻时就到村里了。老丈人在村里积的有德,帮过很多人,来村里之后日子过得还可以。开点儿田,种玉米,年轻时也去山下的县城里呆过几年,后来老人身体不好,就回来照顾他们了。老侯说他虽然是倒插门女婿,村里人没有欺负过他,对他还是不错的。六、七十年代很苦,几次都差点死了,都是村里人救的他,他一辈子都记得。他说:“你看,这几年你们每年来我家住,我也可以挣点钱,村里人有不少人眼红呢,也没为难过我,不容易的。”我说:“是啊,不容易的。”我怔怔地看着他,因为我脑海中有一个疑问几年都挥之不去:这样的艰苦之地,为什么他们不下山呢。我坐在崖壁边歪着头问老侯:你们为什么不下山呢。老侯依然充满内容地望着我笑——朝阳的第一抹红光照在他的额头。老侯站起来说,“快看,太阳要出来了。”
话语间,第一缕橘色的朝阳像金粉般洒向了西南边的崖壁,我也兴奋地站了起来——这是我见过最明亮的橘色,照射在红色页岩崖壁顶端。这一幕让我心中的“壮观”一词的精神世界又一次拓宽,光与岩石撞击散发出无以替代的、热烈的光芒,既有“光”,也有“芒”,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下去了。太阳升得很快,崖壁的红光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扩大,东边的山是紫色的,天际线是蓝色的,向上依次为粉色、橘色,直至蔚蓝。
日出奇观精彩、短暂,很快天就白了。老侯露出了更白的牙齿笑着招呼我:“天亮了,我们回去吧。”第二天回程,在五脏六腑都要被颠出来的大客车上,我还在一直想:为什么他们不下山呢。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在我心头才开始渐渐有了一些答案。
土卫二
同样的1997年,“卡西尼”号探测器升空,开始了人类探索土星的历程。在古罗马传说中,土星是以农神Saturnus的名字命名的,从前3世纪开始,与希腊神话中的克罗诺斯混同。在希腊传说中,农神吃掉了自己的孩子,宙斯是他幸存的孩子。在如今的天文研究中,希腊传说中的故事很可能是发生过的事情——土星吞噬过自己的卫星。对于土卫二的近距离观察收集到的标本数据表明,喷射的羽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进一步的研究推测土卫二上具备地球生命所需的几乎所有元素。公众开始议论这颗星球是否拥有孕育生命的潜力,人类有可能奔赴这个似乎符合所有地球生命需求的星球吗?
2005年的一天,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陶瓷工作室和吴永平、安然扎飞镖,正难解难分,导师吕品昌先生推门进屋,对我说:你去美国吧。我正在投出飞镖,还是掷了出去。扎在标盘上之后,我说“好”。吕先生说你去外事处和晋华老师接洽。我说“好”。两个“好”之后,彼时的我既不知道要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
在一片恍惚中,我购买了美联航的纸质机票,于2006年到达罗德岛设计学院。起初住在波士顿我父亲的研究生崔蕾先生家。崔蕾先生一家给予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每天坐小火车往返学校与住处之间。
我以为中央美院的同学们就算很用功了,到了罗德岛设计学院才知道什么叫用功。任何时候去教室,都是灯火通明。雕塑系的整栋楼是二十四小时不休息的,任何时间都可以来工作,设备是免费的,原料需要自己购买。大楼像一辆一直开动的火车,陶瓷、玻璃、金属铸造等等制作性强的专业都在这栋大楼里。我想大家一定是觉得罗德岛学费昂贵,所以格外珍惜学习时间吧。刚开始上课麻烦就来了——雕塑系的课程材料中是没有泥巴的。对于在中央美院以泥塑教学为基础的人来说,没有泥巴怎么做东西呢。教授对我说,课程中所用材料均为直接创作,金属、木料、玻璃等等,需要泥料你可以去陶瓷系买。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建筑和平面设计也是顶尖的。因为在建筑系工作过,我也经常去建筑系看看。他们的建筑系四年级以下是不允许使用电脑的,有限的图面表达是为立体表达做准备的,也没有我在建筑系所教授的绘画课,基本都是做模型,这与我在国内建筑学院的工作方式大相径庭。向教授们和同学介绍的环节,我信心十足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教授们和同学们看完ppt还是很有兴趣,也提出了问题。系主任布什教授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是你展示的中国教育非常好,但你认为一些很好的作品,在我看来非常相似;第二是为什么几乎所有人都在做人像作品呢。
布什教授是个热心肠的白胡子老头儿,一个真正的好教师。我们俩经常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经常一起吃汉堡,“鸡跟鸭讲”讲得很热闹,讲完各自刷卡结账。每次我能感觉到他那颗热乎乎的心,温和、有幽默感,又能阶段性地提出尖锐的问题。他说:“你的技术很好,可是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的方法,你还没有找到你自己。”这么尖锐的话我不知该如何理解和应对。布什教授跟我解释,“作品就是人,你看70年代也在罗德岛读过书的奇胡利,他的玻璃艺术就是他自己,很夸张、很绚丽,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一个天才式的探索者。”布什教授坐在桌子上边说边作怪动作,边比划,生怕我听不懂。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一定要相信,没有人会是一样的。”我能感觉到布什教授在保护我的信心,又要鼓励我的决心。他帮我制定学习计划,说你有这么独特的母体文化,能表达很多东西。又很严肃地说:“我并不知道你要怎么做,只有你自己知道。”2019年,得知布什教授突发疾病去世的消息,我做了一件作品纪念他。我非常感谢他,是他教我如何初步建立自己的创作方法论。
美国的新鲜感很快消失,问题很快出现。问题不在环境,在我自己。课程中很多和欧洲历史有关的讲述我听不懂,还有很多与基督教或新教有关的事情我也听不懂,需要很多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同学们的作品。我这么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瞬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我明白我不可能用英文来开玩笑,也听不懂同学们开的玩笑。我只能把他们说的笑话大概记下来,晚上查阅字典,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在开什么玩笑。其实也无非是某个篮球队明星的前任女朋友又出什么绯闻之类的,还夹杂着很多俚语,不知道前因后果,不可能听懂,也并不觉得可笑。
于是真的出现了第二天才能勉强笑出来的笑话。
这是什么问题。当然,“诗歌”、“笑话”都是最难翻译的文字,也是对语言要求比较高的表达。最初我想是不是语言的问题,是不是待的时间短。询问了一些在美国呆过十年以上的朋友,他们说呆了十年、二十年也没什么用,语言还是不行。当然吃饭睡觉是没问题的,一旦触及到稍微深刻一点点,或者是不容易表达的意味,困难就出现了。特别是艺术、哲学概念,用中文尚且说不清楚,用英文就可想而知了。语言和文字,不仅是交流的工具,共识的符号,更是精神的家园。
语言当然是障碍,更大的障碍是文化。幸亏视觉艺术是世界性的语言,幸福、悲伤、感动的共鸣有时是不约而同的。布什教授说,我带你看一个同学的作品,调侃说:“你快跟我来,只有你能和他做得一样好。”这位美国同学咖啡色卷发,皮肤白皙,每天准时到,准时走。他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人体,做得好极了。这让我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课程中并没有所谓写实雕塑的课程。布什教授很得意地对我说:“你看,他做得很好,我教不了他,但方法是我教的。”我问你教他什么方法,他说,去博物馆临摹古代的人像雕塑。
布什教授讲,他是个极度痴迷的孩子,你看不到他的时候都在博物馆呆着呢。就这样我们慢慢熟悉了。我的名字郅敏在英文中很难发音,英文中没有“郅”(zhi)这个音,只有“chi”这个音,“郅敏”这个音叫起来很费劲,“chi-min”一会儿就叫成了“Jemmy”,我说“Jemmy”就“Jemmy”吧。我说你就叫我“Jemmy”,我也给你取一个中文名字吧,你的头发颜色很好看,很像咖啡色,“咖啡”一词也是“Coffee”音译到中文的,我就叫你“咖啡”吧。我把中文“咖啡”两个字写下来给他看,他说这个图形很好看。后来,我在美国展览的作品都是咖啡开着他的卡车帮我运送。每次都是他主动说,“不要担心。”每隔几天,我就去他那里看看进度。几个月之后,作品规模越来越大。咖啡做了一个像火山口一样的山,有一米多高,上百个十公分大的各种姿态的人从各个方向在往上爬。他说,你看他们都在往上爬,还要把旁边的人推下去。我问,最后呢。咖啡说,没有最后啊。最后爬上来什么都没有啊。我们俩哈哈大笑。

2021年,郅敏在景德镇创作。
所以我并不认为所谓写实雕塑在欧洲文化中已经绝迹,那是他们的文化方式。我觉得他做的又快又好,技术能力可以达到容•穆克的段位。后来2013年在巴黎看到卡地亚中心容•穆克的个展,看到他的工作方式,我也才真正理解到西方人做写实泥塑人体就像我们中国人早上起来喝杯茶,然后静下来画几片竹叶那么简单,那么自然。这里面存在的似乎还不是技术问题,是骨子里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的问题。回望中国雕塑,由20世纪前中期引入的欧洲雕塑系统是最好的方式吗,也不得而知。咖啡并不是没有老师,他的老师是博物馆,是他们的历史。
在美国同学眼中,我可能仍然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中国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我才深刻领会到中文、汉语对我是多么重要,它们是我全部的精神家园。张光直先生认为“文明动力是政治与财富的结合”。一语中的,但是精神的凝聚是如何做到的呢。多年以后,我看到有几位中国作家早已谈过这些问题,称汉语是自己的祖国,再后来看到海德格尔很早也阐述过相似的表达。我日思夜想的所谓故事、情节、诗意、情绪、思想、精神,都是以中文的方式在脑中编织、构建,无论是文字书写,还是口头讲述,还是在心中默想,都是在重组中文字面之后的精神世界。中文是所有中国人的整个精神家园。
当然,情感也不是都需要语言才能传达。国外生活处处充满紧张感,紧张感来自于因为陌生而无法彻底放松。一上火车或地铁就要盯着看站名,竖起耳朵听。我日复一日地坐小火车上学,小火车开得很慢,和列车员每天打招呼,学会买月票和月卡咖啡券。有一天,我上车之后坐在常坐的位置,照例和列车员打招呼。这时又上来一位年长的乘客,我把座位让给他,我说我马上下车。我换了车厢找位置重新坐下,在谢润湖站,和往常一样下了车。下车之后我看到列车员在车厢中奔跑,车开动了,他跑到我常坐的座位窗前才看到站台上的我,咧开大嘴朝我挥手。我们对望而笑,相互挥手,直到小火车慢慢远去。我想是他找不到我,担心我错过站才满车厢跑找我。在美国确实获得了很多陌生人无言的善意和默默的帮助。
在罗德岛设计学院,我用英文完成了《火山——自然的烧制》的文章,第一次总结出个人对于“烧造”的理解。这是我在美国的收获之一。在罗德岛最后的总结报告中,教授们还是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大大低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他们对于中国的釉上彩、宜兴紫砂和中国的神话都很有兴趣,希望我来介绍宜兴的紫砂茶壶。我说原料一直在都有啊,当然是聪明人发现了这种原料的特性,烧制出这样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的一种高温陶器。这种材质立性很好,透风不透水,适合做茶具。但饮茶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中是无关于解渴的,而是更有关于礼仪,有关于对谈。艺术在等待技术的提高和文化的成熟。对于茶树的认识,茶叶的生产,烧造的水平等技术提高,这需要很长的历史过程。还要等待文化的成熟,进而一步一步产生茶的文化。什么样的茶叶用什么样的水来泡,用什么样的茶壶来盛装品尝?品茶需要什么样的话题?茶具需要放在什么样的家具之上?对谈,就是人和人的交流,人和人坐下来的位置、距离代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茶杯的大小、重量、手感,水的温度等等都需要考量,这样越来越复杂的文化系统就逐步出现了。谈了很多,最后我说中国宜兴的紫砂茶壶应该不会出现于罗德岛。罗德岛太冷了,一阵大风吹过去茶就凉透了。教授们都笑了。一天,布什教授对我说,你可以留在这里,先当助教,我替你争取教职。我不知该如何判断。
我只好奔赴纽约州立大学去找我的姨妈——Amy。
(文/郅敏,来源:北京壹美美术馆)
艺术家简介

郅敏,1975年出生。中国艺术研究院雕塑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委员会委员、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研究与创作、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公共艺术研究与创作。2022年,作品《二十四节气——立秋》荣获意大利第39届佛罗伦萨文学与艺术奖雕塑类金奖。2020年,作品《鸿蒙》荣获第8届“明天雕塑奖”金奖及年度大奖。作品《舟》荣获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2022北京冬奥会国际公共艺术大赛优秀奖”并成为七件落地作品之一。作品《天象四神-青龙》荣获“瓷的精神”——2021景德镇国际陶瓷艺术双年展高岭奖铜奖,作品《河图洛书——出水的龙马》获文化和旅游部“丝绸之路”特别荣誉奖。主持多项全国性大型展览,参加各类学术展览七十余次。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法国巴黎文化中心、北京壹美美术馆等重要学术机构举办过10次个人展览。已出版《发光体——中国的文化与艺术》《无穷尽的创作方法论》等7部专著,主持多项核心期刊的学术专栏,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国家级艺术类核心期刊发表文章、主持专栏共计10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