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发生在丘挺位于北京的工作室。小院内,紫瓦黄墙,令人想起灵隐寺的黄色。小巧的古凉亭内饰有“滴翠”二字,它和这一天的阵雨,和院内顾盼生姿的几棵松树,几乎快要营造出某种宁静的禅意——只要你忽略掉眼前一大扇,堪称“跳跃”的艳粉色院门。


丘挺工作室的小院
对于这扇门的选色,丘挺有他自己的一套诠释:“许多人想到水墨画家,多是黑白灰的调性,比如穿着汉服,喝着茶的传统印象,粉色的院门既是我对这种脸谱化印象的调侃与反叛,其实也代表了我当下的某种状态。”

“性本丘山”展览现场
人们完全可以发现,“梦境”与真实,温暖与晦暗,守古与创新,禅意超脱与种种“不安分”的视觉元素,统统整合并出现在了“性本丘山”的展览现场,成为丘挺在再造的“桃花源”图景中的一部分。
“性本丘山”展览中最核心的作品,当属艺术家新近创作的“桃花源”系列。它脱胎于艺术家与话剧的一场跨界合作。2021年在参观“延月梳风”展览之后,赖声川导演感遇于丘挺水墨中“如梦如幻”的气质,相约合作新版《暗恋桃花源》的舞台美术。

2022年“暗恋桃花源”剧照,摄影:王开
这次合作引发的后续,是丘挺对于“如梦如幻”这一意象在个人创作中的持续拓展,“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画‘桃花源’,源于迷梦的逃离,潜移默化地经由我的潜意识,最终促成了桃花源系列中,走向意象化的几幅作品。”桃花源”系列由此正式成章。
如同莎翁剧目之于戏剧,“桃花源”之于中国画家,意味着创作者需要拿出更多面对经典的勇气。这样一个曾被历代中国画家反复塑造的经典母题,既是每一个中国人内心存在的独特的精神风景,在象征层面,更是中国人所特有的“乌托邦”——在当下,如何塑造“桃花源”,几乎与如何面对当下身处的时代同质。

展览现场
如展览策展人丛涛所说,“通过介入这个题材,丘挺让自己的艺术表达进入到历史文本和图像的序列,‘血战古人’的方式,让他的作品具有了一种超越当下和现实的独特品质。”【1】丘挺无疑选择了一条十分和缓的“血战”路线,这或许与他当下,或者说,与他试图达到并希望分享给外界的心境有关。
丘挺的整个春天因疫情困居江南,错过了《暗恋桃花源》的新版在上海的首演,“错过春天”并不是艺术家的孤例,在丘挺看来,无奈与错过,或许也是一种“兴”之所致。重要的是,“面对当下我们如何把自己调整到一个自我最佳状态,将祥和与悲悯寄托在创作中。”
“桃花源隐喻逃离,这种逃离是主动的,不限于肉体,也包含着精神的失范和游离。”【2】于是观众可以看到,“桃花源”系列中有一棵离奇出走的桃树,也让丘挺基于当下语境的水墨诠释,获得了某种当代性的,属于品钦与马尔克斯的魔幻与幽默的特质。在困顿与苦闷已成为盘踞在许多人心头的主色调时,“桃花源”系列的色彩,不仅撩拨、感染了观众,最先打动的其实是艺术家自己。

展览现场
在面对接下来的采访中,丘挺老师将娓娓道来来:有关“桃花源”系列的缘起,跨界带来的实践经验;对于本次色彩之变的缘由与处理观念,对于“桃花源”的创作理解;如何精心编排一个“声光色味俱全”的水墨画展——包括拿捏影像与水墨质感,以数字生成影像,包括用“叙述逻辑的反推法”创造一块“丘挺石”,以及他从这种图式创造方法中,揣摩出的一套有趣的水墨“数字生产模式”......
最精彩的部分,或许是他从“桃花源”手卷的创作谈起,从艺术本体出发,以“一个艺术家全部的贪婪想法都交给手卷”式的热情,展开他多年来对手卷这一中国画特殊媒介的研究,以及他在穿梭于水墨的传统与当代面向之际,创作经验的深度分享、分析与思考。(孟希)

1 园与源·桃与逃
孟希:您的新作“桃花源”系列脱胎于和赖声川导演合作话剧《暗恋桃花源》的舞美设计,舞台的“造梦”特质,舞台的特殊体量感和面对对象的不同,是否让《桃花源》系列与您以往的创作相比具有某种不同的特质?
丘挺:去年我在苏博举办个展“延月梳风”,赖导看后尤其喜欢我画中如梦如幻的感觉,尤其是我的《延月梳风》手卷中后半段的迷漓恍惝的意象,与他的创作有某种气质上的吻合,这也成为我们合作《暗恋桃花源》的开始,也是这次个展“性本丘山”的缘起。这也让我的“桃花源”系列有着复杂的互文关系,包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暗恋桃花源》的话剧文本,也要考虑舞台空间和我个人艺术手法,首先创作的预设就和以往不同。

桃花源9,138x34cm,纸本设色,2022
进入展厅,大家最先看到的两张作品,是话剧《暗恋桃花源》用在了主海报和门票的设计上。展览中的手卷是为戏剧的舞台布景而作,需要我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暗恋桃花源》剧本这两重文本的重叠中进行。当然,我还需要考虑舞台取景的特殊性,比如画面中前景桃树的高度,需要考虑它和演员身高及舞台中行走的位置关系。
另外,之前的《暗恋》的舞台是由八幅布景构成,演员由左侧进入,而手卷的叙事逻辑和传统书籍一致,都是从右往左,连续不断,边卷边看。赖先生和我经过综合考量之后,希望我能以擅长的手卷的形式呈现会更有趣,赖导说而有了这个长卷之后,他想到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在舞台上,让它从右到左缓缓出现。让演员从右侧进入舞台,遵循了中国传统卷轴画的观看与叙事方式。

桃花源1,纸本设色,68.4x34.5cm,2022

一棵逃树,纸本设色,30x40cm,2022
这批作品与戏剧都采取了“桃花”这一意象。比如我画中有一棵“空缺的桃树”,取自《暗恋桃花源》的文本,剧中就有一棵从桃花木里逃出来的桃树,伴随这棵留白的桃树,演员将讲出台词:“我要这么一棵桃树杵在那干什么?”这种重叠的互文恰恰是我觉得特别出彩的桥段!也从中衍生出许多对于当下艺术境况的反思。比如在叙述水墨本体,拓展水墨外延,以及当下艺术的某种热闹现象的三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2022年“暗恋桃花源”剧照,摄影:王开
《桃花源》是喜剧,《暗恋桃花源》是悲剧,并构的叙事隽永中见悲欢,与赖导合作引发的另一个后续思考,即是我对“如梦如幻”意象的延续。很多艺术家或许都有类似的经历,短期内一直画一个东西,晚上做梦也会想着它。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画“桃花源”,让源于迷梦的逃离,经由我的潜意识转换,最后成为了“性本丘山”展览中“桃花源”系列更为意象化的几幅作品。

桃花源3,纸本设色,68x35cm,2022
孟希:色彩,是展览“性本丘山”中最引人注意的部分,在中国画传统谱系中有重墨与重彩两种方向,并往往认为前者代表文人格调,直到李可染先生以《万山红遍》进行中国画的色彩变革,而您之前围绕山水园林的创作如《与谁同坐》系列大多以水墨为主,这让《桃花源》系列中的色彩与前作拉开了不小的距离——粉色的大量运用,鲜亮柔美,富含情致,是否可以看作您正在尝试的某种创新?
丘挺:是的,其实我一直都在探索水墨画中的色彩,只是大家对我的印象更偏水墨一点。去年我在苏州博物馆的“延风梳月”个展,就有很多用色的作品,包括“与谁同坐”系列有几张大的重彩,《银山塔林》是银笺设色,其实两条线我都一直在做。

与谁同坐,纸本设色,240×200cm,2021

银山塔林,银笺设色,34×100cm,2021
回到这次色彩的使用上,很多处理其实也延伸了我一贯的创作手法,无非就是这次的色彩更容易撩拨人心,也更具指向性。这种转变或许跟当下大家内心的状态有关,面对每个人对于公共秩序产生的焦虑与茫然,越是这样,我反而越认为需要某种靓丽、绚烂的色彩来抚慰我们的内心。我这次展览中有一张小画《雪江》,是心绪飘零时画的这种灰调子的阴郁意象。但展览整体看来,还是处于一种比较温暖阳光的状态。

雪江,25.2x34cm,纸本设色,2022年
“桃花源”系列是比较感觉性的意识流的创作。在粉色调的拿捏上,我也吸收了来自张僧繇、董其昌、恽南田没骨画法的影响。
具体到用色上,大家知道,粉色很容易造成一种“粉气”,这就需要艺术家的把控力,比如控制干湿的反差。此外,我也运用了墨分五色的原理进行色彩的意象性表述,以心理率物理的色域有自己的走势,艺术家通过不断地推演,让色彩层次之间产生呼应。“桃花源”系列的色阶变化并不陡峭,而是在平缓中求丰富,通过层层晕染,形成如同音阶一样的平缓、微妙的粉色调层次,这也是我在色域的整体把握中非常在意的。

桃花源4,纸本设色,50x35cm,2022

桃花源5,纸本设色,51x34.5cm,2022
孟希:《桃花源》系列触及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桃花源”文本,从您知名的“园林”母题,推进至“桃花源”母题,从“园”至“源”,是否意味着某种持续向内心世界推进的创作方向?
丘挺:中国文化本身就讲究“内化”。比如,山水画就是在考究人与山水相融相化的关系。“园林”则是介于有相与无相之间的母题,我笔下的园林有些其实是我生造出来的。园林也是一个“桃花源”,是中国人“落地版”的桃花源。如果说桃花源反映的是陶渊明的个人状态,在其中融合了儒家、道家与佛家的思想,有忧勤,有自托知足,也有乐天安命,桃花源强调的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那么,园林也是如此,它反映了中国人的耕读文化,奋发读书,远行创业或出仕,还乡之后建造一个落地版本“桃花源”,这就是园林。
这个落地的“桃花源”带有很多世俗性,比如厅堂的规格,具体的陈设等等。而作为艺术母题的“桃花源”则是一种人类普世性的乌托邦,如同西方人心中的瓦尔登湖,是一个可以逃离现实制约,内心向往的自由之地的象征。在做“桃花源”系列期间,我当下的某种状态,让我对向内的倾向更有感受力,或者说,这种题材诉求的东西,在我们当下的处境中更为放大化,也让我更有触动。

桃花源7,纸本设色,49.7×31cm,2022
孟希:这次展览中也包括一批写生作品,对这批写生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丘挺:这批作品包括我两年前去丽江和香格里拉画的写生。画丽江也是我对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感兴趣,丽江是少数民族白族、纳西族的聚集地,建筑有飞檐、假山、太湖石,可以说很有江南情致的文人气。

丽江写生,绢本设色,86.3×61cm,2020
另外一部分写生,是我的一些小画,以近似于偶裁的形式,画我工作室的小院,画小院里的一座古老的日本塔,几棵松树。这些松树的姿态与顾盼,都经过我的反复挑选。写生既是我个人的书斋潜心,也是一种水墨日常性的实践。就像今天大家拍照发朋友圈,水墨的多样性也包含这些日常化的创作,应该和人用筷子吃饭一样,进入创作者的日常。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将这批写生纳入了这次展览。

耦斋写生1,纸本设色,27.5x18.5cm,2022

春天里,纸本设色,27.3x18.5cm,2022

六义园1,纸本设色,27.3x18.5cm,2022
2 艺术家可以把所有最贪婪的想法交给手卷
孟希:您刚才也谈到“桃花源”系列与舞台空间关系的考虑,很多长卷都具备空间性,甚至是带有“舞台意识”的,您这次的手卷《桃花源》的创作,是否与中国画历史中的图式有某种上下文关系?与您过去的手卷创作有何区别?
丘挺:这次手卷的创作,主要从我个人对于传统图式的积淀与理解出发,加上话剧的文本,当然也包括历代画桃花源母题的创作。“桃花源”是一个被历代画家反复创作的母题,每个人的叙述都是一次重构和再造,甚至是颠覆。如传陈居或仇英的作品,以及文徵明、陆治、钱榖、査士标、石涛、黄慎的桃花源图等等。——具体图式来源,或许早已说不明白。
我观看和画手卷的经验比较多,对手卷的课题研究有偏好,也算是手卷创作最多的中国当代画家之一。我认为在今天中国多样化的艺术样式发展中,大家对于手卷的重视是不够的。单纯从现代艺术的形式、视觉与心理层面来看,手卷是一种非常完美的形式,其中包含很多艺术本体性的价值,值得我们去挖掘。
早年我在浙江学习期间,就很想以手卷形式表达杭州灵隐寺。当时我住在灵隐寺附近的金沙港,可以在开放时间之前,先游人一步观赏灵隐寺的景色。灵隐寺的特别之处是水,溪水从北高峰而下经飞来峰,流经金沙溪,汇入西湖。夏天的时候,低处温度较凉,水面温度升高,水汽升腾,在灵隐寺间形成一层飘飘欲仙的雾气。我画了一些小幅作品,形成了我90年代中期一批不错的作品。我也一直试图将灵隐寺画成手卷,试过一次,总感觉画得不好,这给了我一种挫败感,成为我后来不断创作手卷的重要动机。

一溪云,38x79cm,纸本水墨,1998
后来我来到北京学习,发现八大处、香山和京西等地颇有古意,我再一次激动起来。那段时间我常在八大处喝茶,酝酿画意,画成了手卷《八大处纪遊》,这也是我第一个比较成功的手卷。这件作品参加了2004年上海双年展“影像与生存”,除了我,同场展出的基本都是影像艺术家。相比中国人,反而是西方人对手卷的兴趣更大。他们对手卷本身的叙事逻辑,对发生在“一米”之间的动态观看感兴趣。我们都还记得2008年奥运会的舞台形式,以及春晚对《千里江山图》的应用,但相比形态,我更看重中国传统文本阅读和观看方式中的实验性与当代性。

八大处纪遊,34x816cm,纸本水墨,2002(局部)
在我看来,手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从装裱到观者上手观看的心理状态,从考究的包首到观者永远不会知道的谜底——画芯的搭配,它们共同组成了一套非常完整、考究的系统。
比如,包首用什么绫锦?是什么纹样与色调?带子、题签是什么材质色调?别子是玉还是什么材料?这一系列精心设置的入场,如同电影开头精美的字幕。随着观者的展开,卷首题字往往出自一位声望学问俱佳的人,而他的提字将为后续内容,起到提升并引入具体关键词的作用。再经过两段隔水,隔水为什么要两段?为什么两段隔水颜色反差不能太大,但又必须不一样?最后来到题跋,既有好友、藏家的题跋,也有雅集中朋友唱和的题跋,于是形成了一个朋友圈之间的状态记录。如果是一个流传有序的传统手卷,人们还可以从题跋中找到收藏、流转历史中的鲜活线索——它在哪次聚会中被拿出来展示?有哪些人曾出席品评?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生动的历史画面。
以上这些,都是手卷设计的巧妙之处,它通过材质、节奏的控制、手的触感共同感染人心,让观者的整个状态安静下来,当人的心、手、眼达到一个统一平和的状态,“火气”自然就慢慢消了,进入到真正的观看状态。
还记得在十几年前的一次展览开幕后,我们有一个小型的雅集,大家一起看我的《西山岚色》手卷,陈丹青先生感叹道:“手卷实在太牛了!你可以把艺术家所有想法中最贪婪的一面全部呈现出来。”的确如此,艺术家可以把所有贪婪的想法交给手卷,并且以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十分诗意的方式全部呈现出来。
手卷的叙事,是它生命的生成与叙事逻辑的生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中不断延伸展开的过程。电影也是如此,观众基于已知的故事跟随叙事。手卷的观众同样不能预知尚未展开的部分,需要他们在脑海中不断进行画面的构建。去年我的个展“延月梳风”,也正延续了我这种从手卷创作中获得的艺术经验。


“延月梳风”展览现场
贝聿铭先生在设计苏州博物馆的时候,开有一扇大窗,在我印象中,除了赵无极展览中曾把窗户全部打开,之后就一直关闭着。透过这扇大窗,人们可以看到竹影婆娑,感受晴雨变幻,窗外与内部空间共同构成了一幅动态的极美的画面,这让我有了借景的想法,想把半封闭了十几年的窗户全部打开。我画了一张带有竹影的手卷《延月梳风》,特地将它置于窗下,让画中拙政园的风景,伴随窗外的竹影展开,苏州博物馆背后就是拙政园,从而让展览真正进入在地性的文脉,与其时其地的氛围和气质,产生了真正的呼应。这种“与谁同坐”的意象,恰恰就是我从手卷中所延续的创作理念。


“延月梳风”展览现场
孟希:如您所说,手卷关乎仪式感与身体性,也是一整套完美的系统,是否可以成为水墨当代性的某种延展方向?
丘挺: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从艺术家实践的角度谈水墨的当代性。认为水墨兼具的多种状态:日常性、世俗性、仪式性、超越性等等。也包括叙事性的逻辑,题跋其实既有日常化和仪式性,也具有实验性和未知性,它是艺术家设计的一个“局”,供知晓规则的人们在其中玩耍。而每个人的不同演绎和最后呈现的不同可能性,则构成了中国画传统中的未知性与开放性。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水墨兼具的各种特性,不是通过简单的转换来获得当代性。创作者必须有一定的学养、眼界和手头创作段位,才能把其中当代性的东西升华出来。这也是东方艺术中特别“娇气”的地方,它充满未知和实验性,同时又具有一定门槛,是值得艺术家进行不断研究与阐释的重要问题。
2011年,由吴洪亮策划,我和徐坚伟的双个展“观”,我们尝试以手卷的创作原理完成整个展览的空间叙述。展览仅展出符合传统观赏习惯的手卷和册页,我为展览题壁“观山、观水、观人,是合一,还是两忘了”的心物相合。展览采取预约制,只邀请心性相投的人前来参观,我们又把古代观看手卷的形式,通过版画的形式贴到墙上,并且安置了一个播放影像的茶室,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观看影像。希望通过展现中国艺术特有的创作与欣赏方式,对今天美术馆系统的现代性和民主的观看方式进行反思与挑战。


“观”展览现场
3 如何“把竹子种在5G的时代”?
孟希:与“延月梳风”展览中您广泛采用纸本、绢本、金笺、独幅、组画、屏风等等不同材料和形式的尝试相比,“性本丘山”在媒介上则更显多元,纳入了音乐与影像,试图调动观者更多的感官参与,如何运用“声光色味俱全”的媒介拓展中国画的传统境界?您如何处理新媒介与中国画传统的平衡?
丘挺:我前不久在中国书画频道主持过一次论坛,题目是吴洪亮先生引用西川先生的一句诗——“把竹子种在5G的时代”,竹子是东方神韵的象征,在5G时代竹子如何生根发展,其实也是中国画与中国艺术如何走向未来的问题。
我一直喜欢影像,尤其关注亚洲艺术家的影像作品,我们这一代艺术家的视觉资源一部分就来自摄影与影像。我认为水墨的气质在影像之间的重构与转化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因此在这次展览中,我选择沿用桃花源“落英缤纷”的意向,与上海的限像新媒体工作室合作,创作了《桃幻》这件影像作品。
这件水墨影像作品的关键,在于如何在跨界实验中探索传统水墨所不能实现的新的可能性,在保持中国画雅致、温润有厚度的色彩呈现的同时,探索与新媒介之间不断推演与生成的维度。我看过很多与水墨有关的影像作品,不乏观念很好,但落地环节常有欠缺,比如折枝与石头是什么关系?顾盼应该是怎样一种状态?空间的“远”如何巧妙运用等等,这需要有挑剔与敏锐的视觉修养。
我把控的重点在于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呈现并拓展水墨的质感与神秘性。影像作品根据图形学算法的层层推演,由氤氲的墨韵引入,墨色的走向与形象建构,与我绘画的肌肉记忆和手部勾勒的惯性有关。如何拿捏墨色层次和纯净度也十分重要,我要求团队制作出的墨色效果不能发“闷”,黑但要透亮。
在接下来进入色彩的表述时,根据桃花源系列的颜色,提取了一些元素,通过计算机生成不断生长的树与花瓣,形成一棵桃树由具象到意象再到抽象的过程。最初的推演方案是从具象到抽象,最后再回到作品的形象——一棵具象的桃树。我认为还是应当任由数字化的桃树生长,越无边无际越好。不为这件影像作品设限,而是寻求一种开放性。通过复杂的编程,让“落英缤纷”飘向更让人意外的表述,这也是我与限像工作室做这件影像作品考虑的核心。整个影像的节奏在算法的驱动下与音频数据信息产生互动,进一步探索视觉与听觉的共鸣。


展览现场
在开幕现场,我们也做了一款桃花意象的香水送给来宾。影像室仍停留着些许香气,和音乐、影像一起,让桃花源的意向达到某种声光电色香味层面的升华。音乐也是由特地邀请的作曲家张露创作而成,跟作曲家讨论整体氛围的时候,我希望音阶与色阶相互配合,色阶与音阶同频,都不要太陡峭,通过加入风笛,形成一种悠扬、无调性的氛围。繁花之下,悠长的风笛与琴弦幽幻玄远,衬底却有厚重与渺远的基调。随着繁花散去,黑白水墨的云山似乎形态依旧,却已浸染上桃源的绯色。作品借此希望用当下最鲜活、当代的语言手法,重构一个属于当下的桃花源。

展览现场
展览中还展出了一块我手捏的太湖石。构造这块石头,我采用的是“叙述逻辑的反推法”——这块石头在世上并不存在,而是照着我自己画的一块石头捏制而成,画法也和历代画家有所区别,不像《十面灵璧图卷》可以找到奇石的出处,它是我完全生造出来的,或许叫它“丘挺石”更加合适。出于展览空间考虑,我不想让它喧宾夺主,因此只展出了系列中的一块,今后还会放大成两米体量大小。根据自己头脑中生造的太湖石图式,从图像到造物,和传统太湖石的生成方式形成了某种“反向操作”,在不断的微调中造石,我觉得很有趣。

丘石,28.5x16x9cm,雕塑粘土,2022
孟希:您的展览似乎总有一个“题跋”般的动词,比如“延月梳风”对应“与谁同坐”,比如“性本丘山”对应“兴会”,似乎在强调一种过程。您希望通过这样一次“中国人集体的乌托邦再造”与观众达成怎样一种“兴会”?
丘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丰富性,总是通过某种过程呈现出来,我试图通过新的媒介的实验来探索水墨的多种可能,以一种开放的胸怀来呈现我的“山水之眼”。无论是“与谁同坐”还是“兴会”,我很想探讨的,就是人和物,人和人,人和不同状态之间的关系。我很喜欢养宠物,总觉得一个人对待小生命的状态,其实就是他面对世界的某种状态。
再比如,拙政园中最打动我的是与谁同坐轩。张履谦为了纪念做扇子发家的祖上,将亭、窗、门、栏杆、门洞和匾全都融入了建筑造型,传统文化中从观念到落地全部天衣无缝的设计太动人了!而这种交融和与谁同坐这个词本身,在今天更具有新的现实意义。当下的世界这么混乱,一个对民族、国家和个体的反思与关怀提出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还是否具备某种气度和胸怀,和不同文化、信仰、种族、地缘政治、身份、声望、地位、素养的人同坐?

桃花源6,纸本设色,35.5×95.5cm,2022
那么,桃花源引入的“兴会”,则与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洒脱、诗性、超越性的精神有关。春天我因疫情困居江南,无法返京,有很多无奈与错过,或许这也是“兴”之所致吧。重要的是,面对当下,我们如何把自己调制到一个自我最佳状态,将祥和与悲悯寄托在创作中。桃花源系列中的色彩意象,对观众的撩拨也好,感染也好,首先是我先被它打动了,才能打动别人。
参考资料:
[1][2]展览前言《丘挺的桃花源》,丛涛
(来源:中央美院艺讯网)
画家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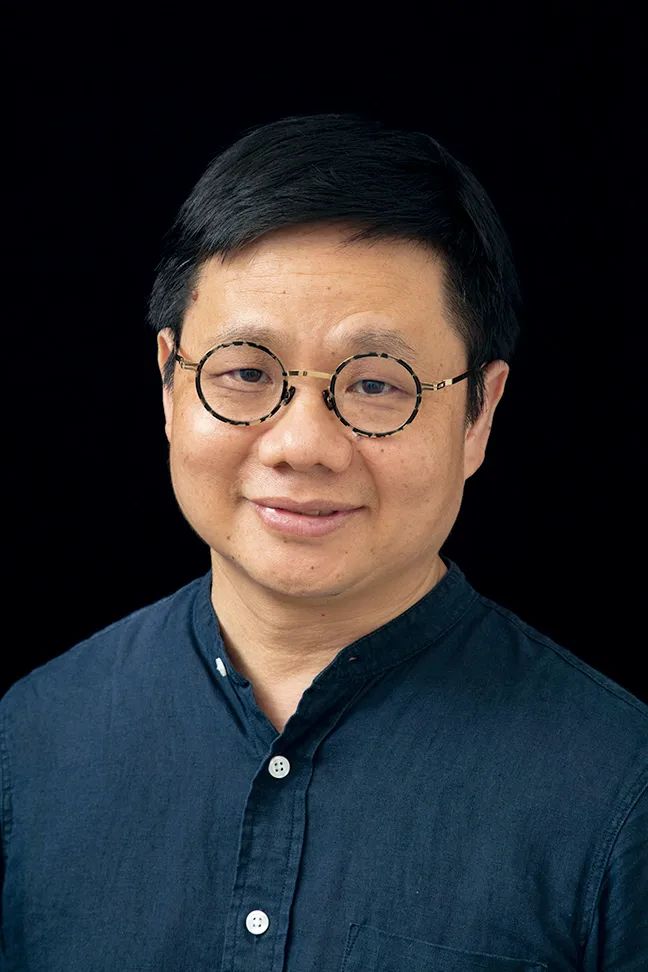
丘挺,1971年生于广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致力于中国画语言的探索与理论研究,注重各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
书画作品被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加拿大安大略省博物馆、法国布列塔尼联邦委员会、浙江美术馆、广东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等重要机构收藏。出版的专著及画册有《延月·梳风—丘挺作品集》《丘园养素—丘挺书法集》《山水画笔墨技法详解》《宋代山水画造境研究》《中国当代艺术家谈艺录—丘挺卷》《丘园养素》《丘园养素一桂林黄姚写生册》《山水之眼》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