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在前面的话
今天是正月初二,向朋友们拜年。
我的《中国农村40个春节》从1977年记到2018年,这40年分成了五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照片,后面我都写了一段话,叫“摄影者说”,也就是我为什么拍下这些照片,怎么留下这些照片的。现在把这些都拿五段话写出来,也是一个曾经的摄影家的心里话,对民族的感情,对农民的感情,对春节的感情。

邓小平在1982年谈起农村改革时对我说“你有发言权”,大概因为我一直在农民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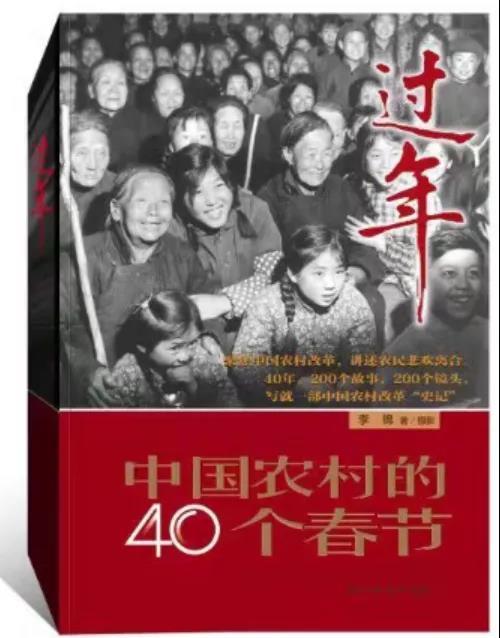
1976-1978摄影者说:
是贫穷与饥饿,对改革做了广泛的动员
我是1971年4月在部队开始搞报道的,1976年到新华社当记者,是专门跑农村的记者。不过一手拿照相机,一手拿笔,两者兼顾,别人说叫“两翼齐飞”。
那时候,公家配备一台旧的德国禄来照相机,后来用上徕卡,用的胶卷都是黑白的,有照相机的很少。

农村改革初期,李锦骑着自行车到农村过年
70年代拍照片,我在济南军区工程兵还是有点小名气的,摄影技术是很好的了,构图、光线掌握得住,还获过一些奖。那时候,年轻,二十四五岁,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是想拍出好照片,可是我在现实中,在矛盾中,日日不能自安。出现在我们报道的总是“莺歌燕舞,形势大好,比任何时候都好”,这是“文革”的口径,可是看到的想到的与我报道的,反差很大。
我是记者,记者算是自由度较大的职业,通常是一个人下乡,可以到自己愿意去的地方去,有机会了解农村的真实情况。不像机关,层层叠叠,都有好多人看着,要请示汇报。1978年是一个大灾年,农村群众生活非常差,吃不饱,穿不暖。面对农民贫穷落后的现象,我一次一次按动快门,留下农村改革前的照片。
改革不是一下子推开的,有的地方快些,有些地方慢些,沂蒙山区就比鲁西北平原慢些。所以到了80年代中后期,沂蒙山区农村还显得落后些,有一些照片是这一阶段拍的。
从当记者下农村起,我就知道春节是农村最重视也是最热闹的时候,农民生活过得咋样,情绪咋样,这时候是看得最清楚的了。我从1975年回过老家,直到1980年才回江苏老家过年,这几年春节一直是在采访中过的。
从1977年起,一到腊月二十七八,我便赶到农村过年。连续在农村过了23个春节,搞了23年的春节报道。苦是吃了,这么多照片也留下来了。照片告诉我们一个结论:是贫穷和饥饿,对农村改革做了最为广泛的动员。
1978-1984摄影者说:
到深水中“抓活鱼”,抢“第一个浪头新闻”
从1978年到1984年,我每年到农村调研310天左右。
农村改革是在探索中逐步明朗的,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央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这当然也包括新闻记者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推进。作为农村改革过程的参与者,我知道重大问题是怎么提出的,中间遇到什么阻力,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有什么经验与教训,对于探索过程,我有认真的思考。
1984年我到中央党校学习时,写过一篇文化文,我强调的重要观点有:一、农村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是一个时期替代另一个时期的转折点;二、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农民革命,是一场亿万农民再次争取主人地位的群众运动;三、农村改革实质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一次冲击,重点是打破一套“左”的机制、体制和制度的束缚,进行制度创新;四、农民自始至终是这场改革的主力军,所有重大创举都是由农民提出与完成的。

从具体报道来说,1979年我在章丘采摄的《棉花姑娘的喜悦》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被评为新华社一等图片好稿。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就是到第一线去抓活鱼,到老百姓中找新闻。1980年,到菏泽、聊城、德州、惠民等鲁西北地区20多个县调查与采访,最早发现并报道“万元户”等现象。特别是1980年秋后,我找到30多个故事,一个故事一个家庭,说明一个观点,这些照片都加上标题,不少登在《人民日报》头版,作为独立新闻发布。《鲁西北棉花大丰收》大丰收为《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采用;《棉花县长散传单》《冒尖户王本跃与他的书记朋友》等形成广泛的社会反响。
农村一些新的苗头,很多是我最早发现并且用图片报道出去的。当然,不是我照片拍得多好,我的朋友王建民、钱捍、候贺良照片都比我拍得好,而是新闻抓得好,特别是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作风引起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关注。报道的茌平县杨庄大队农民写出《庄户人家好记者》的表扬信。1981年12月,高唐、茌平、齐河、平原、陵县、宁津等县相继写信给党中央与新华社,赞扬我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事迹。1982年,我向邓小平汇报农村改革情况,被邓小平认为“你有发言权”,胡耀邦总书记对我深入群众调查深入出批示,作为改革开放后新闻宣传工作者的典型开展学习活动。回顾这8年人生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最没有拘束、发挥最好的时期。

我写了最早的论文《到深水中抓活鱼》《论第一个浪头新闻》。从1979年到1984年,《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图片与文章达99幅(次),是全国记者中最多的。
1986--1995摄影者说:
“山东出典型”,我是农村典型的调查者
1984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半年,接着到中国新闻学院读书到1986年。以后的整整8年,是我的“闭关”时期,长期在基层蹲点调研。从1989沂蒙山区九间棚的调研,到1996西藏农村的调研,每年我都是一个人独自在企业和农村住50天以上。这阶段,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组织建设、农村私营经济,这些变化因为我身处在一线,总是第一时间捕捉到。当时流传“山东出典型”,基本上是农村典型,这些重大典型的调查我几乎都参加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沂蒙山区平邑县九间棚村调查,1989年7月至12月,住到九间棚村调查52天,提出“九间棚精神”,后发展为“沂蒙精神”。还有滨州的“兴福现象”的调查,我一次就在村里住了48天。


1994年2月,李锦在山东省博兴县兴福镇农村采访。从1993年到2002年,作者在兴福镇蹲点调研8年,总结混合所有制经验的“兴福现象”
从1988年到2004年,我担任山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17年,还是中国新闻摄影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时候,以文字为主,先搞特写,每年春节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特写,在春节写特写,整个新华社,恐怕没有比我写得多的。到了1989年起,我便以调查报告为主了。到1995年,以理论研究为主。不过,摄影也没有丢下,断断续续。这一阶段,农村变得丰富了,也复杂了,毒品、贩卖妇女等现象也出现了。对于农村发展中这种泥沙俱下的情况,我也拍了。
1996-2007摄影者说:
世纪初农村调查,内参被批示37篇
从1996年5月到2000年6月,我到西藏四年。在拉萨过了两个春节和藏历新年。写了很多特写,也拍了很多照片,我觉得藏历新年与春节是相通的。我也在纳西族、白族、苗族、傣族、侗族、壮族、哈尼、基诺、回族人生活的地方过了春节。春节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传统,春节民俗像一条流动的河,正因为流动着,正因为有许多支流,它才具有了生命的活力。春节民俗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大的河流,它像中国老百姓心上的长江黄河,是任何其他民俗不可替代的。

1997-2008年,是农村改革处在平缓发展的阶段。中国加入市贸组织,加上城市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加快,发展很快。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两位高整增长阶段,然而农村改革却慢了下来,城乡差距在拉大,农民生活显得苦了起来。进入21世纪,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发表在春节前夕,政府加大对农村投入,城乡统筹被视为“第三次改革”的主题,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也没有得到官方认可。农村改革大改上处在停滞状态。但是有一件事很受农民的欢迎,就是免除农业税。农民作为弱者的现象似乎重返,政府对农村开始关注。这一阶段,我又回到山东,写出兴福镇农村新阶层入党调查,写出《山东农村合作经济调查》一组4篇,写出东营和谐社会4篇调查,新泰市农村平安协会调查。其中包括莱州三德建设经验、李沧区网上执政能力调查、武城县监督“一把手”调查、沂水生态养猪经验、青岛法院救助受害人制度、泰安打击黑社会做法等调查报告。2008年,中国新闻社山东分社王鲁平请我帮助办内参,一年37篇内参调查被领导批示。农村的政治、党建、文化、科技、法律、民族与社会稳定,都成为我调查的内容,我拍的照片,也是方方面面都有。这一阶段似乎一直是勤快的,但是轰轰烈烈不起来。

2008年1月,李锦在山东沂水调查农民生物养猪情况
到了2008年,我已经连续在农村过了23个春节。
2008-2018摄影者说:
2018年春节跑了四个省
2009年3月,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党中央负责同志,建议中国停止天量贷款,防止金融风险加深,得到高层批示,并引发一系列文件出台。从那时,我的精力与时间转入整个财经与国企研究。我自己的价值追求是“历史趋势的发展力,国家难题的破解力,社会进步的引领力”,眼界更高了。尽管仍然是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常务理事,但是仅是挂的名,因为当时我的身份是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从此后,我的事业转移到北京,重点从事国资国企研究。这时候,我离摄影已经愈来愈远。只有在春节回家看望老人时,或者到边疆旅游时,不由自主打开手机。到云南、广西、海南,随手拍些少数民族过春节的照片。常常是以一个退休老人的爱好去拍些东西。不过捕捉时代的形象变化是我难以舍弃的习惯。有时拍照片,自己还是用心的。

2018年2月,在沂蒙山区的费县万良庄,作者李锦向老年农民了解新一轮改革产权制度落实情况
我的根在农村,从2015年起我在沂蒙山区平邑县九间棚村建起书院,这是我蹲点的村庄,我成了山中人,与农民朝夕相处。因此还被评为2015年中国十大读书人物。

到了2017年底,石油工业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40个春节一书,猛然觉出,新时代的变化太大了,自己拍得太少了,不能留下历史的空白。于是在农历二十三从北京直接到沂蒙山,先去山东费县、平邑,后回济南,再经浙江台州,到广东珠海,最后来到河北乐亭,走一路拍一路。这几个点,具有不同特色,还新写50篇文章配上,对我来说,是一次补课。用新时代的眼光审视农村的变化。用一个人拍的照片记录和揭示中国农村40年的变化,我做到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我天天是紧紧张张的,5月完成了《中国力量》写作出版,6-7月完成《过年》的整理写作,8-9月完成《见证改革四十年》的写作,接着是中国国企改革40年回顾。忙一点,但是很充实,而文字上精雕细刻,是做不到了。
近十多年,我已经不习惯用照相机了,全部用手机拍摄,像素小一点,不讲究了。不过,这终究是为40年农村改革,能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了。这构成我思想生命的另一世界。
《过年》中的两个故事的案例

三十年不舞的龙灯
1980茌平
来到我的采访根据地茌平。因为人熟地熟的缘故,我很快了解到农村改革中深层次的东西,自己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
茌平县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比较早,在1980年种植棉花时,几乎全部实行土地包干,农民情绪高涨,都肯往地里投入,有的人家实在拿不出钱,就把门板和房子檩条拆下来卖掉,换回良种。秋收后,遍地出现售棉热潮,全县28万亩棉花单产由35斤一下子增到80斤,预计全县农民人均收入由原来的46元增长到80多元。丰收后的农民忙着舞龙灯、跑旱船、踩高跷,宣泄他们的情感,这是沉闷太久的一种爆发,显得异常热烈。
在李寨村,一件小事引起我思想的强烈震动,使我心海起伏,很难平静。
李寨村农民在丰收后舞起龙灯,全村人都跟着忙乎,很热闹。当宣传部副部长窦有德与新闻科张宝海、杜长之领我到李寨村时,群众已在队场上舞开了,我拍了几张照片后便爬到看场人住的房顶上,想拍张大场面的照片。拍了几张,舞龙的人步伐慢了下来,有时绸布缠在一起,拉扯不开。后来,舞龙人坐在地上,不舞了。当时天气很冷,人坐在地上呵的气都是一团白雾,看得见。我在屋顶上站久了,腿酸身子也冷,一会儿手指便冻僵了,不听使唤。陪着我站在屋顶上的窦部长急了,把手套着嘴,吆喝着场上人站起来快舞。这些人舞了一圈又停一来,窦部长生气了,跑下房顶准备训斥这帮舞龙的人。可是,他下去后很快又跑回来,爬上房顶,向我解释,这帮人都是老头,体力跟不上。村里三十年没舞龙灯了,还是“土改”那年舞过,现在的年轻人都不会舞,这些老人就是“土改”那年舞龙灯的一帮人。
“土改”时舞一次,包产到户又舞,整整三十年,窦部长的介绍,一下子引起我的注意。我马上下了房顶,与这些坐在队场上的老人们聊起来。我先把这12个老汉的年岁问了一遍,最大的是掌龙头的李庆华,“土改”时49岁,今年79岁,最小的“土改”时19岁,今年49岁。12个老汉平均年龄63岁。
李庆华讲起“土改”时那一次舞龙灯的情由。当时每家都分到十几亩到四十亩地不等,平均约30亩。工作队把土地证发给他们,这12个贫苦农民都掉了泪。李庆华当夜把土地证贴在心窝上,睡着了。祖祖辈辈没有土地的农民有了自己的耕地,大伙都想乐一乐。全村人每户出5斤粮食,第二天买回颜料和布,龙重新舞起来了,引得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热闹,大伙一边看,一边喊解放了,翻身了,那场面热闹得很。
打从互助组后,硬要大伙牵牛人社日子一年过得不如一年,想乐也乐不起来。包产到户,土地又是自己的了,出多少力,就收多少庄稼。不搞大呼隆了,人出力,地也长脸,棉花产量去年平均每亩只收7斤,今年一下子涨到109斤一亩。23年没有分过一分钱的李寨人从队里人均分到现金120元。粮也有了,钱也有了,老百姓又过上解放初的好日子了,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了!“土改”时就是这12个人舞的大灯,大伙又相约着,乐一乐,三十年不舞了,路子有点生了,年纪也大了,腿脚不灵光,舞不动了,舞一舞,歇一歇。李庆华说,自己是土埋到脖子的人了,哪有心劲玩啊,翻身了,图的是心里爽快。
“第二次翻身,第二次解放!”在平农民口说出的,是我最早听到这种意思的话,时间是1980年12月。第一次听到这层意思,确实感到新奇,有种震颤袭击自己的心房。以后,邓小平讲“第二次革命”是1985的事。
“第二次翻身!”我与窦有德、张宝海相视一笑,都体味到这句话的含义。窦部长说:“又翻身了,还不舞欢些?”老人们一个个爬起来也不掸衣裳,说声“加把劲,把三十年的力气都使上”,舞了起来。举彩球的李庆华引龙头追逐,忽而贴地而行,忽而俯首直扑,忽而陡昂头,引得围观的群众眼珠不停地转悠。陡然间,李庆华高喊“翻身了,解放了”,其他老汉也一齐跟着喊“翻身了,解放了”,这是1949年冬天他们齐声呐喊出来的。三十年后,他们再次喊着“翻身了,解放了”,周围的群众不停地喝彩、鼓掌,舞龙灯的人情绪高昂,围观的人也兴致盎然。
李寨村的农民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看成是“第二次解放,第二次翻身”,是对他们自己生活质朴的感受,也是理性的归纳。然而,这正是整个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况的写照。在整个20世纪,中国农村发展最快的便是
这两次解放,后来被认为是“二次革命”。

我发现中国最早“包产到户”村庄
1979茌平
这块石碾子,已经转了几百年了。到了1978年12月底,这块石碾子突然停了,石座也塌了。这里的农民搞包产到户了,搞的时间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是同一个冬天,同样是在1979年春节前。小岗村搞包产到户是1979年5月后才被公社书记发现的,而在平马坊搞包产到户的时间比小岗村早半年,发现人是我和在平县委书记管春梅。
茌平是黄河北边一个穷县,出义和团的地方。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会后,我到这里了解农业学大寨的情况,没想到碰上马坊生产队偷偷搞包产到户的事。
到马坊调查也是一种偶然。在茌平采访七天,确实找不出在学大寨方面有什么值得好报道的。我常到县招待所西边集市上抓拍一些照片,那时集市刚开始恢复,多是露水集,一会儿便散了。无意间,看到两个老人说的很带动,听的也入神,眼神瞟来瞟去,象是怕别人听到什么,不时用手套着耳朵,不知在叽咕什么。
我走近与一个老人背靠着,听得清楚的是“这下好了”,“咋啦?”、“分啦”,“咋分”,“包产”。“上头不查”,“背着”。
发现我在旁边,老大爷警觉了。问“干嘛的?”我脱口问“有红枣买吗?”“没”,老人说了声便骑上自行车顺茌平大街往北踏开了。
我急步跑回县委招待所,在传达室掏出七角钱租了辆自行车,眼盯着前面的老大爷追过去。大概有二十分钟,到了一个村子,老大爷进了巷子一拐,就找不到影子了。
走到村中央,看到一个妇女在石碾子旁纳鞋底,头也没梳,篷头垢面的。走了好几家,发现男人们都下地了,老人多去走亲戚去了。村子断墙残垣,满眼是黄土,有的塌下一块,也没有砌起的。
一个老汉倚在墙根晒太阳,问队长在哪,他说“没啦”;问会计,他也说“没啦”。他说,自个管自个,包地了。看我不走,想和他啦呱,他便说村里有两项是全国先进:一项是计划生育,都是光棍汉,不要抓,人口就减少了;一项是财务管理,队里嘛也没有了,只有几条要死的牛,不要管了。俺是先进,可没有人来为俺来评比。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分开,不行。
经过了解,得知马坊村是三进工作组的“老大难”村,难就难在村政权建设上。这是个由两大姓为主组成的村庄,15户,58人,110亩地。生产队长由大姓轮留坐庄,“你唱罢来我登场”。然而,“文革”后庄里风气变了,没有人肯当队长了。队里没有一分钱公积金,只剩下一把旧算盘,还有十来斤谷子,拿多少工分也没有现钱分,队长说话没人搭理了。何况,县里公社里年年组织到外地挖河,老百姓不肯去,上头派民兵来绑人,队长也得陪着,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骂,把人都得罪光了,谁还愿意揽这个差事啊。
要说难,难在穷上。打从1958年吃饱自产粮食,马坊村已连续21年吃国家统销粮。从1966年起,没有打过油。土改时从地主手里分得九头牛、两头驴,后来入了社,现在大队还是九头牛,不过有三头趴在地上总起不来,瘦得肋条骨挑着一张皮。村里孩子成天围着扔土块,嚷着要吃牛肉。1978年这个生产队棉花亩产只有7两,粮食亩产71斤。吃不饱饭,庄子也留下住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村里饿死11个人,为了破产度荒,后扒东屋。社员李德安在两年里先扒南屋,扒掉六间房,最后又出去要了三年饭,保住一家人性命。土地无人种,生产上不去,生活没着落,来年冬春再逃荒。如此年复一年,恶性循环。“马坊马坊,十年九荒,腰里没钱,屋里少粮。女的外嫁,男的逃荒。”这是村里好事人编出的。
转折发生在寒冬里。秋播播不下去了,队里还有不到20斤孬谷子,拿什么去播种?管区派来学大寨工作组坐阵催着。国庆一过就下种,可一个月过去了,马坊地里还是白板一块。工作组要换队长,可全村中年人都轮着一遍当过队长了,谁也不肯出头。
一个老太太的下跪,使马坊人命运发生转机。选举会开到深夜,工作组长说队长选不出来不让回去睡觉,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着,谁也不吭声。有人提出,“就像兄弟们一样,日子过不下去了,分家吧”,工作组长不吭声。鸡叫的时候,煤油灯芯跳,快灭了。一个姓王的老太太从人群中摸到台前,扑通一声跪在工作组长面前说:“分开过吧,过不好,俺要饭也不登你干部的门。”组长说:“你把公社的脸往那撂?”老太太说:“俺饿死也不说是马坊的人。”组长脸转过去了,老太太就是跪着不起来。她是村里辈分高的老人,整个会场开始骚动,有人站起来。在场的管区书记愣了,也不敢发火,光吸烟,不吭声,猛地站起来,推门走了,工作组长脚跟着。有人喊“咋办”,组长甩下一句“看着办”,也走了。精明的会计一声喊,“他们不管,俺分队”。
事情快得出人意料,仅仅几分钟,两大姓就分成两个队。这时有人提出,一家亲戚也不要为早上工、晚下工的事吵了,索性分到底。人们为快要熄灭的灯加上油,也不嫌夜长,当下这十五户人家分成六个组。不是父子组,就是弟兄组,有的单门独姓的,一家就是一组。大伙申明,以后是各家管各家了,自己种自己收,队里不管分配,可土地是国家的,皇粮国税还要交,明年秋上收公粮,按地敛,上河工按户摊。
马坊村中间有块空地,有块石碾摆在一侧,村里人都到这里来碾麦子。可现在没有粮食碾了,石碾子半塌,也没顾得修。他们村刚刚分开不到二十天,队长也找不到了,我拿着照相机在村里转悠,面对这面碾子沉思一会儿,把相机对准石碾子按下快门。一直陪着周主任笑道:“李记者,你成了安东尼奥尼啦。”安东尼奥尼是意大利的摄影记者,“文革”中到中国拍了揭露阴暗面的影片,在西方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面对县委办公室主任的玩笑,我口说:“你们这里黑暗面太多,拍不过来。你说,村庄破墙像不像电影《地道战》上的镜头?如果拍解放前的电影片,到你们茌平来,准能行。”他不置可否地笑了起来。
听说84岁的王老太太就在队场东边的小屋,我走了过去。进门就有一股浓浓的霉味朝鼻子里窜,满屋子黑乎乎的,四壁空空,只有一张毛主席像贴在家中,可也被烟熏得黑黑的,猛一看,竟发现不了。床上一张芦席,没有垫被,被子已说不出补了多少层,好像本来就是由无数补丁缀成的,黑黑的,补丁的红布与绿布也早已变成黑色了。旁人说,这“百补被”是大娘16岁陪嫁过来的,盖了68年啦。老太太不在家,到邻庄的闺女家换良种去了。
老太太没找到,我又回到村中心,拍下饲养员与生产队的牛,这是生产队最后的象征。
拍完照片,我便回济南过春节了,带回济南的是一篇内参稿,标题是“还是大队分小好”。

李锦向滕州农民捐赠“蹲点五十年”展览
1月19日,在滕州市鲍沟镇张埠村的杨华红色文化宣传中心建成。《九间棚精神调研展览馆》《李锦蹲点调研陈列馆》是这个农民办的红色中心的主要组成部分,由180多幅图片组成。李锦来滕州采访50年,这是他对农村振兴的支持,也表达他从事农村调研50年的情结。(李锦,新华社高级记者)

春节,滕州市鲍沟镇张埠村农民到展览馆参观。
